「說『槍不會殺人,是人殺人』,其實是沒有看到全局。
我看到槍的各種面貌,對我而言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槍會殺人。」

文|伊恩‧歐佛頓
譯|陳正芬
有幾種人會用槍殺人。
一種是為了彰顯掌控力,多半是罪犯、幫派份子、恐怖份子、警察或軍人,他們一扣扳機就結束一條生命,目的是為了遵守特定的意識形態或教條,可能是想稱霸街頭、搶劫、維持秩序、想保護國家甚至行使懲罰。奪走他人性命時當然就成了殺手,但他們通常不是為殺人而殺人,死亡只是權力和控制的副產品。
無數多的擁槍者,槍殺他人以聲張個人權力,他們陷入一時的狂熱、絕望、憤怒或自我防衛,於是用手上的槍來奪人性命,有時他們的行為具正當性,但大多不是,殺人多半未經預謀,而是對威脅、狂熱或恐懼的反應,背後動機非常多樣,想了解到底是什麼原因使這些人殺人,就跟了解人生一樣複雜。
有兩種人因為向黑暗面靠攏而想置他人於死地。殺人不是報復、防衛或欲望的副產品,而是讓自己強大的手段,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就屬這類,他們往往是年輕人,暴怒之下在單一的公開場合殺人,他們不屑一般人為了搶劫、忌妒、不滿而施暴,也無視於正義的基本概念。
或是殺手。這群殘酷的稀有品種為錢殺人,但「錢」不是唯一理由,因為他們永遠都找得到其他謀生方式。
當我把關注焦點從生者與者人轉移到手中握槍的人時,首先想寫的兩種人,是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以及暗殺者。
大規模槍擊事件兇手
二○○八年九月的某一天,我徒步經過芬蘭西部某小鎮外圍的濃密森林時,雪開始飄落。
幾天前,二十二歲的芬蘭人撒利(Matti Juhani Saari)做了一件讓人匪夷所思的事,他走進就讀的大學殺死十人,在距離這裡五英里處的考哈約基塞納理工大學(Kauhajoki School of Hospitality)大開殺戒,他手持華瑟P22半自動手槍,頭戴黑色頭套,身穿軍人的黑色工作服,從地下室潛入校園大樓後爬上樓梯,一副在出戰鬥任務的樣子,殊不知他才是芬蘭這座安靜小鎮上唯一的敵人。
當天早上十點半,撒利先走進一間教室開槍,一群同學正在這裡考商業研究,他逐一趨近受害者近距離射擊,接著來到走廊裝填新的子彈後回頭去殺老師。他在教室緩緩繞行,對發出聲音的人送上慈悲的一擊(coup de grace)。
撒利殺了人後,打電話給一位友人吹噓自己幹的事,接著把汽油潑灑在血跡斑斑的地上,扔了一根火柴便走出去,熊熊烈火在他身後燃起,九位同學和一位老師已經沒有氣息,另外十一位在烈焰中受傷,撒利眼看學生們尖叫跑進芬蘭秋天的微光中,之後便對自己的頭部開了一槍。

這是芬蘭史上承平時期最慘重的攻擊事件,共死了十一人,撒利開了一百五十七槍,其中六十二槍在受害者的體內被發現,光是一個人就挨了二十發子彈。
有一發最不令人惋惜的子彈,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發出的最後一聲槍響,為一場另類的競賽鳴槍起跑,記者競相趕往現場報導當下最熱門的話題:大規模槍擊事件。
死亡新聞的階級架構
現代的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和媒體彷彿連體嬰, 新聞記者在科倫拜校園事件、鄧布蘭校園屠殺和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中大肆報導,讓這些地名永遠留存在大眾心中。在新聞界「有血就有收視率」的情況下,當晚全世界的頭條都是撒利血洗校園以及考哈約基,新聞快報出現校園外一排排光影搖曳的蠟燭和泰迪熊,而芬蘭的救難隊不知所措圍成一圈的畫面在全世界放送,槍手邪惡的影片和他醜陋的誓詞,重播了一遍又一遍。
這當然是個大事件,不僅因為這是芬蘭在兩年內發生的第二起大規模槍擊,也因為死的都是些前途大好的年輕白種學生。類似事件在西方新聞界非同小可,因為一則新聞事件要花多少時間報導,取決於偏見和優先順位,也就是「死亡新聞的階級架構」。白種槍手在美國殺死二十名學童,將占據全球新聞的主要版面,二十名成年黑人在奈及利亞的槍林彈雨中喪生,卻幾乎無人一提。若是學校遭到大規模槍擊事件,報導篇幅一律多於其他地方,即使美國企業遭大規模槍擊事件血洗的可能性是其他地方的近兩倍。
換言之,儘管大規模槍擊事件僅占美國所有槍殺事件的百分之一左右,但是就新聞頭條和報導版面來說,衝擊卻相當深遠。
有人說媒體做得太過火,極盡能事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反而鼓勵其他人有樣學樣,讓扭曲的靈魂豁出去幹一場驚天動地的壞事,這種看法有其邏輯。西元前三五六年,希臘人黑若斯達特斯(Herostratus)縱火燒毀以佛索(Ephesus)的亞底米神廟(Temple of Artemis),當時的人寫到他此舉是企圖留名後世,結果還真如其所願,他也是摧毀古代世界七大奇蹟的人,說明犯下重罪也能留名千古;同樣我們也知道蘭薩(Adam Lanza)、趙承熙(Seung-Hui Cho)、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以及可能有一小部份是因為我的報導而認識他們的撒利。
一九八○年代維也納地鐵系統突然爆發自殺潮,之後各大報同意配合執政當局改變報導內容,避免對於跳火車的解釋過度簡化,並將類似悲劇事件移除頭版,標題上也不出現「自殺」兩字,結果當地的跳軌自殺率下降百分之八十,清楚說明了媒體極端行為可能的影響。於是就有人要問了,「如果媒體完全不報導大規模槍擊事件,同樣的事還會發生嗎?」許多人直言抨擊媒體對某些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大肆報導,一位法庭心理醫師對ABC新聞表示,播放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殺手影片是社會的大災難,「簡直就是他的公關影片,要將他本人變成昆丁塔倫提諾片中的人物……影片沒有任何教育意義,只是在認可他的行為。」還有人說,報導槍殺事件令人髮指的細節,幫助「情緒困擾者將抽象的沮喪變成具體的幻想實踐」。
或許這些意見都沒有錯。但媒體的聚焦也凸顯出國家對現行槍枝法律的立法不周全,密集報導考哈約基,促使了芬蘭政府減少核發手槍執照,同時提高擁有槍枝的年齡門檻,這些都是媒體促成的。
現代怪物
一九六六年,二十五歲的前海軍陸戰隊查爾斯.惠特曼(Charles Whitman),攜帶三把步槍、三支手槍和一把槍管鋸短的霰彈槍,爬上德州大學的校塔頂端,距幾小時後他被射殺時共開槍射擊四十八人,其中十六人死亡,也將「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這個獨特的現代怪物介紹給世人。
當然,校園和辦公室屠殺的恐怖災難不是美國特有的悲劇,死傷最慘重的大規模槍擊事件,要屬二○一一年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在挪威犯下的案子,六十九人在瘋狂掃射中喪命,另外八人在炸彈爆炸中死亡。在此之前,全世界最慘重的攻擊發生在一九八二年南韓農村,性格孤僻的警察禹範坤(Woo Bum-kon),因為同居女友在他午睡時拍打停在他胸口的蒼蠅而將他吵醒,一怒之下殺死五十六人。
媒體除了把焦點放在死亡人數和殺戮的頻率,也在那些揮舞槍枝的人身上,人們問:「是什麼樣的人會做出這種事?」很難給出絕對的答案。美國情報機構觀察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後表示,校園槍手並沒有單一的「性格檔案」,槍手間有諸多差異。儘管如此,一般認為他們皆存在某種傾向,二○○一年的研究觀察了美國四十一位大規模槍擊事件的青少年殺手,發現百分之三十四是他人眼中的獨行俠,百分之四十四對武器很感興趣,百分之七十一曾遭到霸凌。
此外,兇手幾乎一律為男性,女性只有少數幾位,其中一位是前郵局員工珍妮佛.聖馬可(Jennifer San Marco),她在加州一處郵件處理場殺死五人,又殺死一位以前的鄰居後才舉槍自盡。至於為何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地方幾乎清一色為男性的原因不明,有些人認為男性在遭遇人生不如意事時會採取較為極端的做法,有些人則認為他們的暴行,凸顯男女體內睪固酮含量與心智發展發的差異,可惜這些理由都似是而非,除了禁止所有男性取得槍枝外,幾乎無助於我們想出如何讓類似殺人事件不再發生。
孤僻的年輕兇手
大規模槍擊案的殺手性格孤僻,他們鮮少兩人一起行動,除了瓊斯伯勒(Jonesboro)大屠殺事件外。在這起事件中,十三歲的強森(Mitchell Johnson)和年僅十一歲的戈登(Andrew Golden)槍殺四名學生跟一位老師,接著又傷害另外十人。但一般而言,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殺手通常單獨行動,且不隸屬任何團體或教派,使當局難以辨識這樣的人並防範於未然。
他們相對年輕,「國會研究服務」(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認為美國的大規模槍擊事件槍手的平均年齡為三十三歲,十一歲和十三歲的極年輕者屬非典型。青少年不會失控抓狂有各種理由,包括孩童較不易取得槍枝、老師和家長往往能在青少年出現令人擔憂的行為時介入,以及年輕的生命往往還沒有那麼多令他們失望的事情等。
我們知道,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通常不善與人交際,他們很少有親近的友人,幾乎從沒有過親密關係,儘管他們有時候會一時「性」起卻不成功,此外他們沒有酗酒和毒癮的傾向,不但不會衝動行事,而且性格恰恰相反。

這些觀察可能讓許多人以為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都有長年的心理疾病史,其實並非如此。雖然他們對這世界都抱持扭曲破碎的觀點,因而鑄下大錯,但心理健康診斷卻完全不足以用來分析某人日後可能成為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二○○一年針對三十四位美國大規模槍擊事件兇手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只有百分之二十三有心理疾病史的記錄。
撇開這些不談,人們依舊專注在這些情緒困擾者的異常心理,評論寫澳洲亞瑟港屠殺的布萊恩特(Martin Bryant)非常喜愛《獅子王》原聲帶;也寫桑迪胡克屠殺多名孩童的蘭薩平日隨身攜帶黑色公事包,其他學生則都是背後背包;我們回想在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殺死三十二人的變態殺手趙承熙,平日喜歡將手機放在書桌底下拍攝同學的裙底風光。儘管怪異,但這些特質完全無法證明日後將成為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有位心理醫師說,「雖然屠殺的兇手往往展現異於常人的行為,但多數行為異常的人並不會屠殺。」
儘管如此,我們大可以說,這些槍手往往非常偏執且不合群,著了魔似地計畫自己的行動,許多殺人魔花幾個月甚至幾年來計畫,例如科倫拜槍殺事件的計畫時間長達十三個月,挪威的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宣稱他策畫行動達五年之久。
這種事前的計畫,反映了他們對世界的仇恨與執念,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希望他們的想法在歷史上留名,而且是透過槍械為自己做出某種辯解。恐怖份子使用槍和媒體來宣揚政治和宗教理念,槍手則是利用槍和媒體來凸顯個人不滿,例如維吉尼亞理工學院的槍手趙承熙,曾經寄給NBC新聞一千八百字的聲明,和二十七段他對著鏡頭怒罵的影片。
另外還有其他傾向。許多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會自殺,許多人身穿軍服,他們往往使用火力強大、射擊快速的武器,「瓊斯媽媽」(Mother Jones)網站檢視過去三十年來用在六十二起大規模槍擊事件的武器,發現超過一半為「半自動步槍,具備作戰性能的槍枝,且彈匣可裝載超過十發子彈」。詹姆斯.荷姆斯(James Eagan Holmes)在奧羅拉射擊七十一人並殺死十二人的槍枝之一是攻擊步槍,具備能裝載一百枚子彈的滾筒彈匣。
使用這類致命武器確實令人憂心。FBI的資料顯示,二○○九至二○一二年間,使用攻擊步槍或高容量彈匣犯下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平均射中十六人,比用其他武器多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三。
以上發現和統計數據顯示情況不妙且令人不安,但在我分析單獨犯下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兇手時,這些只有些許用處。於是我再度檢視這一長串罪犯,從中尋找最能代表這些傾向的人物。
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
我要找的是兇手的原型—相對年輕、獨來獨往且不善與人交際、身穿制服、攜帶高容量彈匣的半自動步槍,這個槍手並未被診斷精神失常,是個寫過憤怒宣言的幻想家。結果這群恐怖人物的文氏圖(Venn diagram)出現一個醜惡且熟悉的名字,也是所有大規模槍擊事件兇手中最兇殘者—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挪威的右翼殺手。

當我來到挪威,想了解更多關於布雷維克的事情時,奧斯陸租車公司唯一能租給我的是輛電動車。我腦中浮現的,盡是某個對地球暖化盡一份環保力量的受害者,在挪威電動車裡因為失溫而凍死的畫面。
電力往下掉的同時, 太陽也逐漸西沉,將最後一道微弱的光投射在深邃的蒂里湖的寬廣湖面上。正當車子以省電的龜速沿著湖邊前進之際,湖水被風吹拂,氾起漣漪,湖再過去是位在最外圍的烏托亞島(Utoya),有些人依舊不願說出這座島的名稱,因為布雷維克就是在那裡殺了幾十人。
就在電力表顯示只能再行駛兩公里時,挪威最古老的客棧之一桑德霍爾敦飯店進入我的視線範圍,這座旅館建在「國王的視野」以松樹圍繞的頂端和綿長蔚藍的湖下方,有一種斯堪地那維亞獨有的美。公會之家擁有十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公尺厚外牆,和門廳外一排嵌著玻璃眼珠的小矮人像,極具田園風光。然而人們不會因為挪威的童話故事或北歐風味的外牆而記得這裡,二○一一年發生的事將永遠留下印記,因為最嚴重的槍擊事件兇手在這裡讓倖存者飽受驚嚇,這些房間裡擠滿哀戚的親友,等待接獲壞到不能更壞的消息,告訴他們子女是如何死亡的。
槍擊案發生的幾天前,以十四至二十五歲為主的六百人,聚集在湖對岸的烏托亞島,舉行一年一度的夏令營,這一群多元且屬於自由派的年輕人,是挪威勞工黨的年輕人當中最被看好的一群,然而來自奧斯陸,三十二歲的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認為他們的包容是背叛,理念是軟弱,於是七月二十二日他乘船來到島上,口袋裝著中空彈,心裡滿是殺意。
晚上五點二十分一過,布雷維克開槍射殺第一名被害者,七十五分鐘後向警方屈服時,已經有六十九人喪命。他總共開了兩百九十七槍,其中一百七十六槍是用儒格槍,一百二十一槍用格洛克,此外布雷維克在小島大開殺戒的一個半小時前,先在奧斯陸政府辦公區引爆肥料彈而造成另外八人死亡,兩百多人被炸傷。
他穿警察制服做出這些恐怖的事,將挪威人心中對政府的信賴玩弄於股掌間,他也戴上耳塞以阻隔槍響。兩個醜惡的事實,讓你對這個人了解許多。
他的殺戮是無差別而且殘暴的,他通常只在有把握射中目標時才開火,他殺人不求快而講求方法,會在很近的射程內對著頭開槍,他對那些躲在樹叢後的人說,「別害羞,」之後便射殺他們。還有些人彼此抱在一起被殺,有些被困在島上的學生勇敢忍受冰冷的湖水想游泳到安全的地方,但他們就像白色的海鷗般被從岸邊的硬礁拉回來,將湛藍的湖水染紅。
在六十九名死者中, 六十七位被射殺、一位溺死、一位跳崖死亡,其中三十三位不到十八歲,最年輕的受害者是來自德拉門的雪若丁.思維巴克邦恩,年僅十四歲。
堅強的信念
我到過全世界幾個發生過類似重大槍擊事件的地方:英國和美國的校園屠殺,索馬利亞和菲律賓的萬人塚,還有亞美尼亞和德國的種族滅絕屠殺現場。那些地方也有種讓人不知所措的寧靜,感覺你問任何問題都是隔靴搔癢且裝腔作勢,對發生過的事沒有簡單的解釋,這些地方永遠具備這樣的特點。這裡也是如此,一朵朵雲飄過來,逐漸縮小天地之間的距離,之後雨勢漸歇,剩下的只有沉默。
夜晚回到燈光閃爍的奧斯陸街道,我徒步經過多間販售廚房和家用品的商店,有白蠟燭、木製地板和北歐的時髦玩意。挪威人不喜歡炫富,這裡的東西既不標新立異,也不會過度裝飾,但是好品味是需要妥協的,萬一你跨越界線,必定得接受社會秩序和輿論的批判,如果你掛上狗打撞球的圖片來裝飾屋子,如果你洗三溫暖卻不遵守正確的程序,會有人對你咋舌並且當面告訴你。
以上是奧斯陸的巴基斯坦籍計程車司機告訴我的,他曾在伊斯蘭馬巴德取得博士學位,自從主管機關替他拍了駕照的相片以來,他就一直留鬍子,因為他在挪威峽灣重新發現了伊斯蘭信仰。他說出潛規則:如果你不喜歡挪威的規矩,最好回到你原來的地方。但是,在全世界生活品質最高的國家之一生活,讓人很難抗拒。
我踏上乾淨的街道時,想起司機的話。我在想,他眼中的忍耐在別人看來是否只是堅強的信念,品味良好和功能健全的社會需要具備並展現自信,但就像光明總有黑暗伴隨而來,或許布雷維克的內心和行為是以最激進、最自我欺騙的形式,來呈現這種集體信念。

我一直在反思這些事,因為我正要前往會見挪威作家奧格.波克格拉文克(Aage Borchgrevink),奧格花了好幾個月調查布雷維克及其殺人動機,我想知道像布雷維克這麼殺人不眨眼的兇手,在他想殲滅的文化之外的地方,是否會搞出這麼大的亂子來。
奧格英俊但不浮誇,他身穿高領灰色毛衣和藍色T恤,很像北歐警匪片中的好人,他的英文無可挑剔,但某方面他也不是典型的挪威人,二十年來他一直在調查巴爾幹半島上車臣、白俄羅斯、高加索等三個地區的人權問題,他律己甚嚴,在挪威以外生活的時間久到足以看清這個國家的缺陷與美麗。
我們在名叫「老少校」的酒吧見面,是布雷維克會中意的地方,我走上櫃台,買了一杯紅酒給奧格,一杯啤酒給自己,總共花了三十美元。我問了兩次才確定沒聽錯,因為挪威的酒稅為全世界第二高,也是維持社會秩序所需付的代價。
奧格端兩杯酒回到桌子,很快進入正題。我們循常規從頭開始,先談論兇手與母親的關係。

奧格解釋,布雷維克的家庭問題被心理衛生工作者完整記錄,當他年僅四歲時,母親便極度恐懼親生兒子會對他人暴力攻擊,於是經常對他說,她希望他死。一九八○年代,心理醫師研判這個害羞的男孩「是母親偏執激進以及對男性性徵恐懼投射下的受害者」。
儘管有這些不利的報告,但奧格說國家根據挪威人對是非對錯的強烈自信而採取不介入,他說當時以生物決定論的信念處理這個案例,認為孩子最理想的狀態是和母親在一起,法院和兒童福利機構都無視專家的警告,於是布雷維克就跟著母親繼續生活。
「是制度把他變成這樣。」奧格說。
奧格認為,未能介入代表錯過機會阻止一個小男孩長大變成問題重重的青年,經過交叉檢驗,連布雷維克都說母親是他的「阿奇里斯腱」,是「唯一能讓我情緒不穩的人」。兇手向法庭表示,他曾經力勸性格孤僻的母親去尋找嗜好,結果她說,「但你就是我的嗜好啊。」
接著是母子關係中有「性」的成分在內。奧格說,社工人員在報告中寫到,「母親和安德斯晚上睡同一張床鋪,有非常親密的肉體接觸,」但是相關單位對此無所作為。布雷維克年紀稍長後,還會坐在母親腿上試圖親吻她,甚至曾經買給母親一根假陽具。
這些童年過往明顯扭曲了布雷維克對世界以及對自己的觀點,「他幾乎就像行屍走肉,」奧格說。「他展現在外的行為非常消費導向,但那是沒有人味的。他用身上的品牌來界定自己,會花一百歐元吃一頓壽司大餐或一千歐元買一件外衣,非常消費無度。」值得玩味的是,布雷維克接受審判期間,挪威的法庭攻防顯然把焦點放在他過去的心理狀態,有兩份關於他的法庭心理鑑定報告,第一份診斷他罹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導致心神喪失;另一份報告診斷他屬多重人格失調,且特別強調自戀和妄想的特質,換言之他是在正常的精神狀態下犯罪,結果法庭採取第二種觀點。
另一方面,媒體緊咬歐洲右翼極端主義、網路助長年輕人走向偏激,以及警方在那黑暗的一天沒能先發制人等議題,唯獨漏掉一個重點。

「關於槍枝法管制的辯論並不多,」奧格說。這令我訝異,在美國,大部份的殺人魔都會引發槍枝管制法的辯論,但挪威絕大多數的焦點卻擺在社會以及布雷維克的成長背景。
就連布雷維克都親口表示,槍和軍事器材是整個殺人計畫的核心。當時他必須克服一個問題,因為在挪威取得槍枝不太容易,於是二○一○年初秋他到布拉格待了六天,因為他以為捷克共和國的槍枝法在歐洲各國中較寬鬆,在那裡能買到他要的格洛克手槍、手榴彈和火箭推進榴彈。
布雷維克離開挪威前,甚至把他的現代汽車後座移開,騰出空間來擺想買的槍,但他什麼都沒買到,後來在文章中寫到布拉格「根本不是買槍的理想城市。」他唯一「成功」的,是在那裡跟人上床兩次。
回到奧斯陸後,布雷維克總算透過合法管道買到武器,他在自白書中表示,他之所以買得到,是因為他「無犯罪記錄,有打獵執照,並且已經擁有兩把槍達七年」,二○一○年他又取得一把槍的許可,那是一把要價兩千美元的點二二三口徑儒格迷你十四型半自動卡賓槍,他說他買來是要射鹿的。
接下來他想要一把手槍,但取得手槍許可就困難許多,必須證明有定期參加射擊運動俱樂部才行,於是從二○一○年十一月至二○一一年一月,布雷維克在奧斯陸手槍俱樂部上完十五堂訓練課,每上完一堂,他醜惡的計畫就愈來愈接近終點,宛如蜘蛛好整以暇等待大開殺戒。
一月中,他獲得許可購買格洛克手槍,便向一位美國供應商買了十個可以裝三十發子彈的步槍彈匣,又在挪威買了六個手槍彈匣。
接下來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
槍呢?「不是重點」
或許是因為布雷維克花這麼多時間來武裝自己,或者因為廣大群眾不願意相信槍械在這場屠殺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因此在殺人事件後的辯論中,槍並沒有成為焦點,挪威雖然曾短暫禁止購買半自動步槍,但狩獵業者的遊說顯然能左右政策制定者,於是這方面的法律就悄悄地被取消,如今挪威依然准許人民購買半自動步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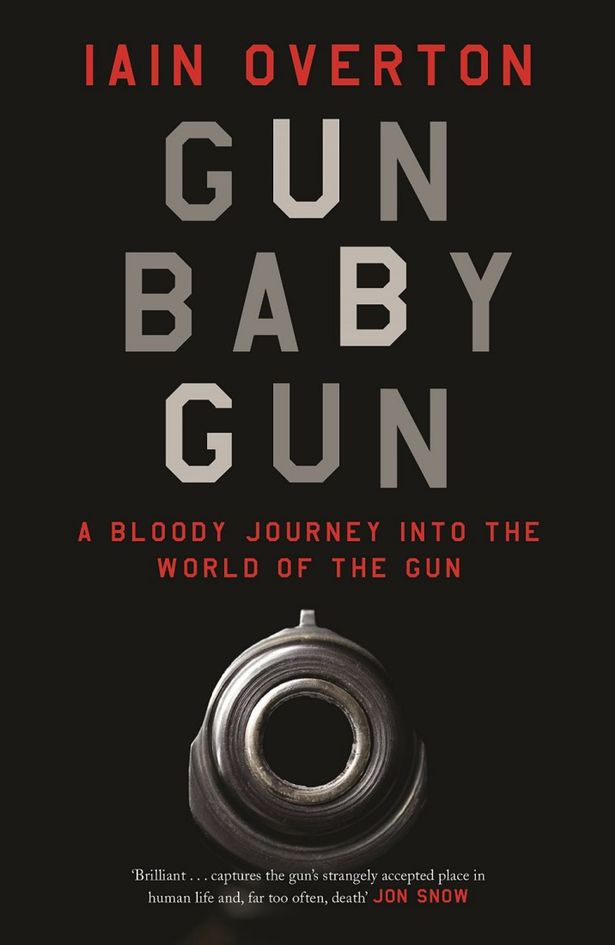
在一個看似讚揚理性辯論的國度,這些突然令我覺得怪異,被布雷維克殺死的人數之多,部份歸因於他將學生困在島上,但他能連番開火而無須停下來扳動步槍的扳機,必然使他射擊的孩子們更沒有時間跑去樹林避難。
像挪威如此自信滿滿的社會,為了理解布雷維克的所作所為,必須把更多心力放在個人的失敗、他的母親和警方的反應上,而不是國家的槍枝法律或他們身為一個國家的失敗。或許這才是正確的反應,畢竟不能讓一個擁槍的白癡來改變人民的生活方式,否則壞人就贏了。
我在這些想法中向奧格道別,槍擊屠殺事件的兇手帶來的黑暗,正逐漸占據我的關注,愈是往深淵裡瞧,就愈無暇顧及其他,於是我把焦點轉到另一個同樣邪惡的地方—暗殺。
即使是槍枝法最嚴格的英國也出了有名的殺手,桑塔.桑切斯.蓋爾(Santre Sanchez Gayle)是英國最年輕的殺手,他年僅十五歲時,為兩百歐元的酬勞在倫敦哈克尼殺死一位年輕媽媽,但他被坑了,因為研究人員發現,一九七四至二○一三年間,在英國雇用殺手的平均費用超過一萬五千歐元,最高十萬歐元,而兩百歐元當然是最低的。
當然,殺手開槍有好幾個理由,金錢必定是唯一的動機,「別以為我跟你有仇,」這是槍手用挖土機把不斷顫抖的會計師帶到偏僻樹林時台詞。
但是,當殺手的行徑被利用來追求「權力」時,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問題將我的注意力和研究帶離職業殺手和變態殺手的邪惡心靈,朝向黑社會槍手更精細算計的恐怖行徑,也就是用槍犯罪的範疇。
(本文為《血色的旅途:權力、財富、血腥與兵工業,一場槍枝的生命旅程》部分書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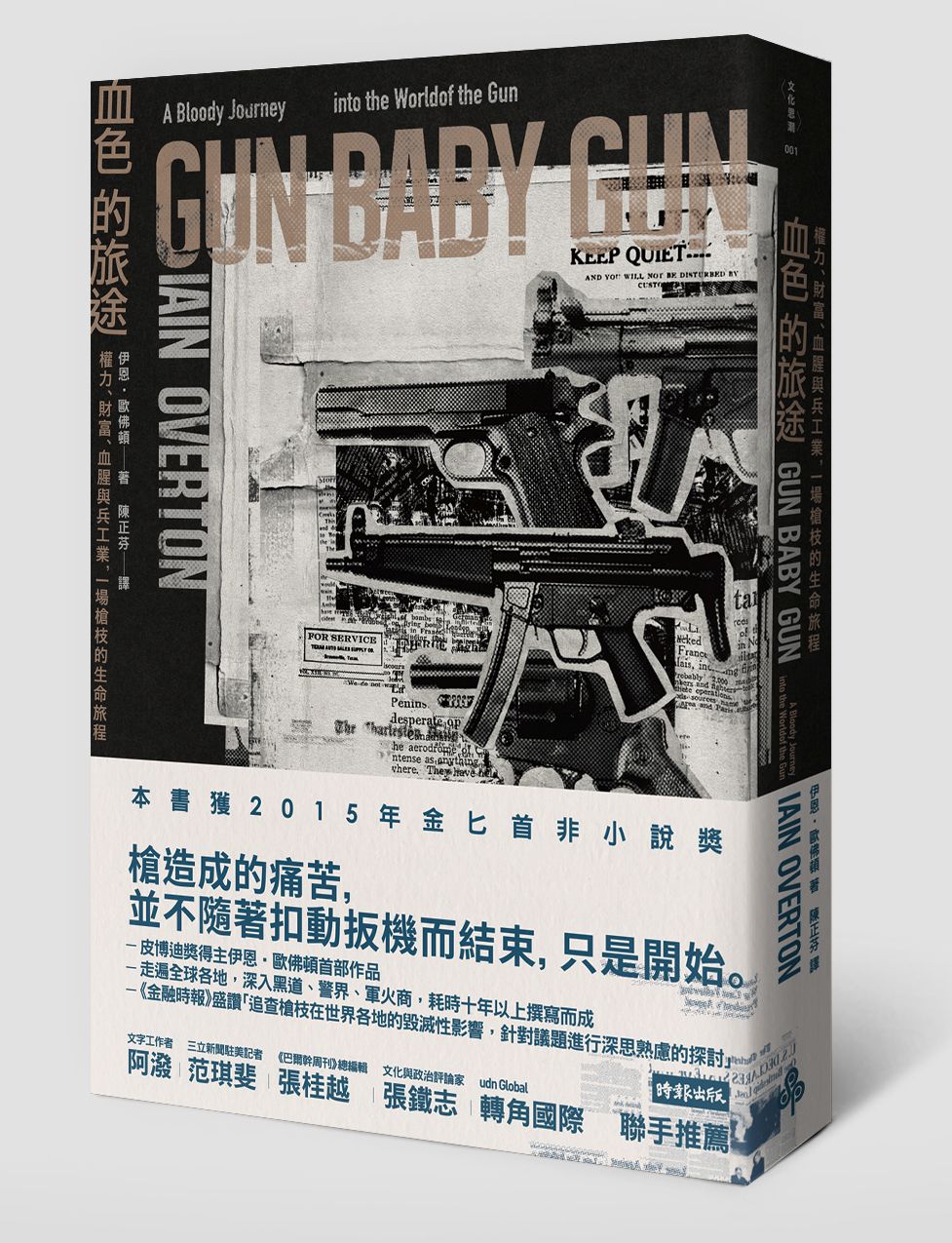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血色的旅途:權力、財富、血腥與兵工業,一場槍枝的生命旅程》 Gun Baby Gun: A Bloody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the Gun
作者:伊恩‧歐佛頓(Iain Overton)
出版:時報文化
日期:2016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