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育和
科層,或黑格爾被遺忘的洞見
警治(或,公共權威)會傾向把一切可能的事物都圈入它的管轄中,因為在這一切物事中,也許會有一些要素可能在某個面向是危險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警治的工作可能不太能變通,會干擾人們的日常生活。儘管這一切相當煩人,卻無法畫出一條客觀的線來。
──G. W. F.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234, Add.
在進入格雷伯(David Graeber)這本嚴肅但不失有趣,反思「科層」(bureaucracy)現象的《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前,也許我們首應重拾黑格爾(G. W. F. Hegel)對「警治」(police)或「公共權威」(public authority),其實也就是廣義的科層、行政與官僚的洞見:以市場為核心的市民社會,如果要能自我治理,個體需要的交流要能相互滿足,財產權要能得到保障,乃至於事物的流通狀態要能維持常態,我們免不了得需要「不太能變通,會干擾日常生活又相當煩人」的科層。而讓這位據說勘破歷史終結的思想家有點苦惱的是:我們甚至不知道怎麼為科層惱人的干涉畫下界線。
為了保護市場教條,市場至上論者把現代社會中科層的擴張,歸咎於民主政治,就像米賽斯(Luwig von Mises)被奉為經典的《科層制》(Bureaucracy)中所說,在經濟市場中失敗,但在政治民主中有投票權的魯蛇,加上想用行政手段解決魯蛇社會問題的善意,才造就了通往官僚集團失控膨脹的地獄之路(頁32)。實情是,在市場與效率原則幾乎宰制公共政策論辯的今天,我們得做更多的文書作業,應付更多的科層行政人員,一次次在表格文書往來之間,覺得自己像個笨蛋。而科技的發展並沒有改變這樣的困境,我們只是換成在網上填寫各種表單,在電話中不停被轉接。
如果市場至上論者表面上的教條是「市場與科層絕不相容」,背後的潛台詞是「自由與民主也不相容」,所暗示的是我們其實只有兩條路走:要麼選擇市場帶來的自由,要麼選擇民主帶來的科層。格雷伯要用這本書破除的就是這個迷思,他強調,科層在當代的擴張與市場原則取得宰制地位密切相關,正是堅持用市場手段解決一切問題的貧乏想像,才創造出一個令幾乎所有與之打交道的人都挫敗不已,「科層最糟糕的元素,與資本主義最糟糕元素,惡夢般結合」(頁29)的愚蠢體制,格雷伯將黑格爾對於市場與科層的洞見,改寫成「自由主義鐵則」(The Iron Law of Liberalism):「任何市場改革、任何政府打算減少文書作業並強化市場力運作的計畫,最後都只會導致這樣的結果:法定規則、文書作業與政府官僚的總體增加」(頁34)。
同樣語出黑格爾:「凡是現實存在的,必有其理據」,科層體制的當代擴張並不是天外飛來的意外,當中反映的,不只是我們所生活的新自由主義境況,還有把暴力隱藏起來並常態化的宰制結構,更涉及我們對「政治」的根本思考與想像。
這是格雷伯從「自由主義鐵則」出發,所探討的三個主題:(1)科層體制的全面擴張與資本主義從七〇年代以來的「金融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在金融資本主義的「新積累過程」中,以「經理人階級」為主體的科層體制,在規訓、穩定與掠奪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的重要作用。對於當代新自由主義如何運作有興趣的讀者,無疑可從導論與第二章中得到啟發;(2)支撐科層運作,窒息一切想像與溝通,導致「結構性愚蠢」(structural stupidity)的暴力。不管這是物理上直接的暴力,還是層級體制中的結構暴力,所造成底層對於「詮釋勞動」的負擔,都鞏固了既有的不平等。關注暴力隱而不顯結構的讀者,則可以在第一章中看到格雷伯對於這個問題的深刻反思;(3)從科層現象延伸出來,對於各種涉及暴力、制憲權與法的後設「政治」論題。對政治理論的研究者來說,從第三章與附錄的《黑暗騎士:黎明升起》影評,以及格雷伯所說的「主權、行政與政治」三分思考,則別有跨領域的思想激盪。
債務人就是經濟人的最高階段
「人不再是被禁錮的人,而是負債之人……一種新的宰制體系正漸漸地全面襲來。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通過在監禁處所對抗種種規訓的歷史經驗,而串連起來的工會是否還有一席之地?能適應新的控制社會嗎?還是得讓位給新的抵抗形式?對於未來的抵抗形式,我們又已經做好準備了嗎?我們能夠抵抗營銷學話術嗎?有許多年輕人對於『被激勵』有莫名的渴求,他們一直在找出奇的培訓與延續不斷的學習,就像上一輩人得耗盡心力,才能發現誰真正從規訓中獲益的人,他們的任務是得要發現他們到底是為了什麼做這些事。蛇的紋路遠比鼴鼠的洞穴複雜。」
──Gilles Deleuze, “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ies,” pp.181-82.
去年(2015)是《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上映的三十週年,三十年後我們不免細數,三十年前所構思的科技成真了多少,結果令人沮喪。我們沒有倒進垃圾就能啟動發電的家用能源反應器,只有自助加油沒有自動加油機器人,體感遊戲至今仍只存在科幻電影中,更不用說懸浮滑板與飛天車了。不過,雖然沒有遛狗機器人,但我們有了無人機,類似指紋辨識的技術也已廣泛運用在日常生活中。顯然有些科技實現了,有些仍舊是幻想,這當中的差別何在?
這並不是因為某些科技構想實在太天真,而是因為當代資本主義內在的運作邏輯,決定了科技發展的方向。格雷伯這麼說:「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似乎出現一個重大的轉向:資金不再投入與另類未來相關的科技,而是投入可以強化勞動規訓與社會控制的科技」(頁120,譯文略有修改)。所有可能導致社會動盪,挑戰權威結構的「詩意(poetic)科技」,幾乎都沒有進展,反之,一切強化管理與控制的「科層科技」則有長足進展,無論是用於戰場的無人機,還是實現各種編碼的生物辨識技術。
科層體制在晚近三十年的成長,必須從七〇年代開始的「金融(生命)資本主義」(financial [bio]capitalism)轉化的角度來理解,資本更多是被挹注到對於非物質勞動──生產非物質性財貨,像是服務、文化產品、知識或交流的勞動──的規訓與組織〔註一〕,而不是被挹注到改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直接生產過程上。而企業的獲利,主要也不再來自於市場,不管是商業的流通或者產業的發展,而是來自於將非物質勞動的產物,各種交流、社會關係與合作形式,納入複雜的金融算計中並榨取其價值。例如,格雷伯非常關注的美國教育體系產業化,就是藉由學生借貸體系,從學生「未來的勞動」這個典型的非物質勞動中搾取利潤。或者,就如格雷伯直白的說法,這是:「來自於他人的債務」(頁51)。
為了讓複雜的金融財務算計體系可以運作,並保證非物質勞動的再生產條件,新型態的「市場」反而需要更多的「管理」,因此,市場去管制化表象的背後,其實是為了更綿密控制各種非物質產生產的社會關係,企業也從這個規訓與組織的過程中獲利,伴隨這個過程出現的,是更多的管制、法令規章與認證,結果就是科層管理組織的膨脹。
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盲點突破,我們總下意識認為「企業管理」代表效率,但卻沒有意識到,要讓企業化的管理可行,得先建置一組行政管理程序,以及一個終日與各種表單、評估、文憑、證照與認證文書為伍的管理階層,上述種種結合起來,其實就是我們認為最沒有效率的科層〔註二〕。
格雷伯用「全面性科層化」(total bureaucratization)來指涉這一整個公私部門逐漸融合,充斥各種規約與規範,終極目的是以獲利之名搾取各種財富的過程(當然,他更偏好稱之為「掠奪性科層化」)(頁44)。他強調,對於科層的批判,得要關注這個「金融化、暴力、科技與公私部門融合,彼此之間是如何交織成一個自我維繫的網絡」(頁75)。
在這個網絡下的新時代科層,它的典範形象不再是我們熟習的,在卡夫卡小說裡面穿著灰色法蘭絨西裝,死氣沉沉的「官僚」;而是以企業「管理」者自居的「經理人」;以及德勒茲(Gilles Deleuze)眼中,讓我們的年輕人鎮日培訓、學習與「被(迫)激勵」,操持「營銷學話術」(格雷伯稱之為「光彩奪目但空無一物」的各種企業慣用語:願景、優質、利害關係人、領導統御、卓越、創新、策略目標、最佳方案)的各種人力激勵、資源與策略部門〔註三〕。
大學也沒能在這波「企業化管理」的浪潮中倖免,格雷伯的經驗談是大學師生花在行政文書作業上的時間,在過去三十年呈現爆炸性成長,讓師生耗費最多心力的不是學術研究與討論,而是應付各種據說可以增進效率與產能的評鑑、進修與研究計畫。
這個由龐大企業化科層支撐出來的「市場」,已經不再是古典自由主義與經濟學所推崇、藉由個人私利與交換而有效率滿足需求的體系。得自己想辦法透過各種認證的人力資本化,取代了勞動,而「維持競爭力」的訓令則取代了交換〔註四〕,國家與社會政策的首要考慮則是極大化收益(通常只是複雜的會計遊戲,特別是在承接銀行債務後大喊國家債務危機,再緊縮公共支出,聲稱使用者付費的偽善把戲),換個角度來看,新的「市場」型態其實不過是一個全面滲透到個人社會關係,以效率、競爭力與企業精神為號召,再從各種虛擬或實質債務中獲利的「管理」體系〔註五〕。

早在一九七九年,傅柯(Michael Foucault)在《生命政治的誕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的講座中,就已經提示「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概念的轉化:從古典自由主義對於勞動、理性與交換的關注,轉化成如何尋求強化自身競爭利基與加值的人力資本形象,這種「企業」形式普遍化的作用「是將供給需求,以及投資成本利潤的經濟模式延伸,使之成為社會關係與自身生存的模式」, 包括了「個人與自身、時間、周身一切、團體與家庭之間的關係形式」〔註六〕。
格雷伯要補充的是,讓市場至上論等右派鼓吹的經濟人模式可以運作的,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科層體制,而其後果是背上各種虛擬債務:無止盡的進修、認證與證照,以及實質金錢債務,「得不斷科層化自己生活,把自己當成小型企業來管理,衡量收入與支出,不斷努力使收支平衡」(頁52)的債務人〔註七〕。
債務人就是經濟人的最高階段!
反傅柯的K
《城堡》中的K的突出特點就是他只對普遍原則,那些所有人都有自然權利的事情感興趣……由於他的要求不過是一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他無法把它「來自城堡的恩賜」……在這個一切人性與正常的物事:愛情、工作與友誼,都被人扭曲成不知從哪裡恩授來的禮物的世界裡,他是唯一正常和健康的人……K的古怪不在於他被剝奪了生活的基本必須,而在於他對這些東西的要求。然而,K單純而堅定的目標,打開了一些村民的眼睛。他的行為使人們知道人的權利是值得為之奮鬥的,城堡的規則並不是神聖的法則……
──Hannah Arendt, “Franz Kafka: A Revaluation,” pp.72-73.
如果格雷伯對於科技與科層間關係的反思,是要說我們不應過度高估科技的角色,那麼在科層與暴力這個論題上,他要說的就是:我們也不能低估暴力在形構當前社會體系所扮演的角色。
閱讀格雷伯,很難不注意到他對傅柯這位當代權力論述偶像的挖苦。格雷伯構思的這個虛擬情境,差不多概括了他對科層與暴力間隱而不顯關係的反思:在圖書館鑽研傅柯各種學說的研究生,終於洞悉到原來組織現代生活的各種權力部署(dispositif),不再依靠決斷生死的強制力量,新的權力型態日益從在地化與去中心化的節點來運作,它是生產性的,而不是純粹的壓制與禁止……有一天,當他想在沒有學生證的狀況下,堅持進入圖書館時,他發現自己遇上的是保全的警棍與驅逐。
這個虛擬情境要挖苦的是,在現代社會中,背後幾乎沒有任何知識體系支撐的直接肢體暴力,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在理解科層現象時,它尤其具有啟發。首先,它表明了在現代生活中所有的科層體制背後,都是直接傷害身體的具體威脅在撐腰。我們不該就此打住,在上述的虛擬情境中,比較可能的狀況,其實是圖書館員或者警衛,在提醒學生下次記得帶學生證後「柔性勸離」了他,而學生也摸摸鼻子回家:不動用直接的暴力,也能達到同樣的效果。
從這個虛擬情境中,格雷伯要傳達的是,暴力其實是一種「溝通」行動,只是它是「唯一一種完全不需溝通」的行動形式(頁112),如果可以使用暴力,就不需要進行任何平等的「論辯、澄清與不斷協商」(頁111)。暴力與科層之間的關係,除了科層最終是靠暴力撐腰以外,更重要且幾乎可以跟暴力類比的是,科層完全封閉了任何平等溝通的可能:在上述的情境中,如果持續追問「為什麼沒學生證就是不能進圖書館」,「我能不能進去讀個兩小時傅柯就走」的話,只會換來館員反覆的「規定就是這樣」「沒有這樣的規定」的回應。
科層也許不需要動用終極的肢體暴力,但它所創造出來、對當事人「有意的視而不見」(willful blindness)(譯文略有修改)的結果,卻與直接動用暴力沒有兩樣(當然,科層能夠這樣有意又盲目地無視對方,也是因為雙方不對等的純粹武力)。
格雷伯對傅柯的挖苦可能不太公允,畢竟當傅柯強調必須把康德式的啟蒙論題改寫成對於構成我們周身一切當下的「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好追問這個現實「不被如此這般地治理的技藝」〔註八〕時,我們也可以合理(寬容)地推論,這其中包括了直接面對暴力的可能。但格雷伯可能會想提醒傅柯,在任何一種需要被追問不被如此這般治理的常態化部署中,不同的階層,對於「問題化當下」所要付出的成本,其實有很大的差距。
這個成本,格雷伯稱之為「詮釋勞動」(interpretive labor),意指在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花在理解他人動機與看法的心力(頁111)。在所有的不平等關係中,往往都是權力地位低下、被壓迫的一方,需要付出較多的詮釋勞動,性別關係就是格雷伯認為最好的例子〔註九〕。對格雷伯來說,科層的程序,以及它處理事情的方式固然很愚蠢,但科層的結構性暴力所創造出來,在上者可以有意視而不見對方,在下者則必須付出更多詮釋勞動的情境,才是科層讓我們變得愚蠢沒有想像力,從而需要批判的主因:
結構暴力將會創造極端單向的想像認同結構(lopsided structures of the imagination)。位居社會底層的人們,得要發揮很多的精力,去想像自己所處環境的社會動力,甚至還得想像社會頂層人們的觀點;然而,後者大體上卻能對周遭所發生的一切視若無睹。(頁129)
格雷伯的看法是,「極端單向的想像認同結構」會窒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一切可能想像,從而持續鞏固不平等的關係。從這點來看,格雷伯對傅柯的挖苦顯然更有深意,對格雷伯來說,傅柯所迴避的問題可能是:在部署與主體之間無限的主體化過程中,紛雜多樣的主體如何透過更有想像力,更平等的想像關係,實現團結(solidarity)?
在傅柯的理論故事裡,並沒有打開村民眼睛,讓他們意識到,城堡的法則並非神聖不可侵犯的K〔註十〕。對格雷伯來說,不能忽略的是在以科層為原則建立起來的種種部署中,詮釋勞動的不平等問題,以及其所伴隨,唯有極端單向的想像認同結構,唯有打破科層的束縛,釋放想像力,實現更有創意的連結形式,才是我們的出路:
權力令人怠惰……科層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民主化這樣的權力,但並無法完全擺脫掉科層。它會變成制度化怠惰的種種形式。革命性所帶來的變革,或許意味著我們可以掙脫這些施加在想像力的枷鎖,讓我們能夠忽然理解,不可能的事情絕非完全不可能(頁155)。
奪回重新想像政治的力量
如果迷思暴力是打造律法,神聖暴力就是律法的毀棄;如果迷思暴力設立了疆界,神聖暴力則摧毀一切疆界……
──Walter Benjamin, “Critique of Violence,” p.249
格雷伯解釋了科層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全面擴張,以及我們必須認真看待其結構暴力的理由,最後還必須處理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如果科層這麼惱人,它幾乎讓人擺脫不掉的韌性到底從何而來?第二,我們能夠想像一個沒有科層的世界嗎?
對於第一個問題,格雷伯援引了韋伯(Max Weber)的經典解答,取代家族連帶,家父長權力與財富攏絡的僚屬管理形式,基於公開申明的規則,中立非人身化的科層官僚一旦登場,我們就很難擺脫它,更由於它把持很難被取代的專業知識,所以始終可以占據有力的位置,讓韋伯只能期待政黨、民主議會乃至於克里斯瑪等等依據不同政治原則組織起來的行為者,對科層官僚加以制衡。
這部分解釋了科層官僚的驚人韌性,但格雷伯著重討論的是,在某種程度上,科層制讓人詬病的地方正是它的誘人之處。在科層制中互動的各方,可以只需要處理形式作業,不用付出任何了解對方複雜動機與需求的詮釋勞動,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於一個無法用科層控制的世界,其實感到畏懼,韋伯對理性化官僚難以取代的觀察,固然有其道理,但科層的韌性,可能更在於它反映了我們內心最深刻的渴望與恐懼,投射並許諾了一個一切都可以得到控制的世界。
格雷伯把廣義的政治世界區分成三個不同的要素:一是壟斷暴力的「主權」;二是處理一切法令執行與管理職能的「行政」;三是涉及一切權力互動的「政治」(頁161)。一直以來,我們都在奇幻文學中想像一個沒有行政科層、主權似有若無、絕大部分情節都是關於擁有各種奇幻力量角色之間相互「政治」抗衡的世界。而在現實世界裡,發生的事情則是,嚴格收編一切可能導致失序的「狂歡」,講究階層,深怕被冒犯的當權者──羅馬的軍國主義者、教會道貌岸然的神父、剝削平民的貴族、殖民帝國的文明人──用各種方式壓抑在他們眼中容易失去控制、讓他們苦心經營的秩序與權威毀於一旦的各種狂歡。
格雷伯在電影《黑暗騎士:黎明升起》中看到的是主流輿論對於「政治」的恐懼:一切挑戰既有權力結構,重新找回不被主權與科層框限的「政治」行動,最終都只會是以暴力收場,不管劇情有多麼不合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訴自己「沒錯,體制很腐敗,但這是我們唯一擁有的東西,反正位高權重的人士只要經歷一番駭人的折磨,他們就值得信賴了。」(頁333)。
格雷伯沒有否認,科層的韌性其實正來自這種畏懼失控,「心照不宣的宇宙論」秩序觀:認為沒有規則可循,政治作為純粹作為力量互動的「玩樂(play)原則(以及其所延伸出來的創造力)本身是駭人的」,因而需要有透明且可預測性的「遊戲」(game)規則,也就是用主權與行政加以約束〔註十一〕。於是整個科層得以存在的心理邏輯看起來像是我們忍受「主權」用直接物理暴力撐腰的「行政」結構暴力,來交換讓「只要它是可能的,它就是現實的」的「政治」暴力不要出現。
這是一個在政治理論中反覆論辯的問題:訴諸高於一切憲制權(constituted power )的制憲權(constituent power,換成格雷伯的話,就是訴諸高於「主權」的「政治」),是否只是血腥的暴力展演(看吧,「還權於民」正是反派班恩遂行暴力陰謀的口號)?又,一旦制憲權「常態化」後,是不是不過又成了另一個壓迫性的憲制權〔註十二〕?
格雷伯首先想要提醒我們的是,「任何對於人的境況、欲望、凡常都能以某種方式徹底解決的幻想是異常危險的,那是潛伏在權力與國家偽裝之下的烏托邦幻影。〔註十三〕」我們不應該因為恐懼「政治」,而放棄對於政治生活的另類想像,結果只是將科層這個巨靈交換過來。
再者,不管是在全球正義行動與占領運動,格雷伯親身投入的各種直接民主的組織模式,都證明「重新奪回想像政治的力量」的實踐,絕非不可能,這並不是複製奪取統治國家與科層機器,再次臣服於資本的「舊政治」,而是「在權力面前創造出自主的共同體」,「集體打造自己的規則或運作原則,並不斷地檢視它們」〔註十四〕。更重要的是,如格雷伯所指出,在歐洲絕大多數的社會安全體制,包括社會保險、年金、圖書館與診所,都是由工會、鄰里協會、合作社與各種勞動階級政黨與組織,有自覺地「從舊軀殼中打造一個全新社會」,從基層逐步建立起來的制度〔註十五〕,科層從來都不是我們組織社會生活的唯一選擇。
如同格雷伯在前作《債的歷史 : 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所說的一樣,壓迫性的體制之所以能得逞,都是因為我們覺得別無出路。我們並非如市場至上論者等右派所說,完全沒有出路,現在這個世界的樣貌,並不是什麼自然的事實:「它之所以會存在,是因為我們集體創造了它」(頁89),在這本反思科層現象的書中,格雷伯反覆提醒的是,不要讓想像力對既有的宰制屈服,也不要放棄另一種團結形式的實踐,永遠不要忘記,六八學運時,漆在索邦大學牆上的口號:「一切權力回歸想像力」(All power to the imagination)!這無疑正是左派構思政治的精髓:「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本文為《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導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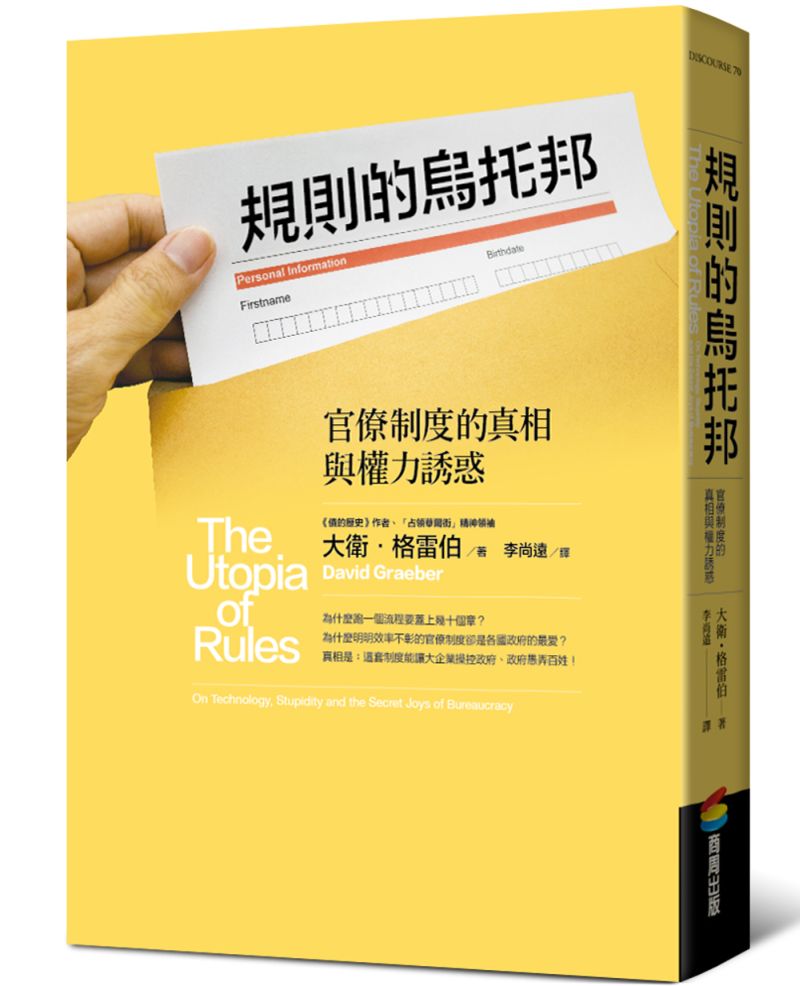
導讀作者註釋
1. Christian Marazzi, 2011. The Violenc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pp.43-64.
2. 其實企業界也不乏類似的自嘲,例如一個經典的笑話是:公司裡有一隻獅子,牠連續吃了十個經理都沒有被發現,直到有一天,牠吃了清潔工,大家才終於發現:原來公司裡有獅子。
3. 格雷伯把這些叫做「狗屁工作」(bullshit job),也另見其短文〈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4. Wendy Brown, 2015. 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pp.62-68.
5. 我們不能單純把這些現象單純視為市場模式的轉變,薩森(Saskia Sassen)的《大驅離:全球經濟中的殘酷與複雜》(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譯本由商周出版)一書,就揭露當前資本主義將無法商品化的物事,驅離出經濟體系的各種殘酷現實,而相較原始資本主義「積累」的「先進」之處,不過就是它是用複雜體系當工具,造就最直接的殘酷。
6. Michael Foucault,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p.242.
7. Maurizio Lazzarato的兩本著作:《打造負債之人》(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與《由債所治》(Governing by Debt)都對這個主題有深刻的討論。
8. Michael Foucault, 1997. The Politics of Truth, pp.28-29.
9. 格雷伯非常借重他從女性主義得到的啟發,他的評論也很值得提:「(女性主義)太過慷慨,往往把重點放在受壓迫者的洞見上,而不是指控壓迫者的盲目與愚蠢。」(頁71)。格雷伯另一篇專欄文章〈Caring too much. That's the curse of the working classes〉也值得參考。
10. 把部署的力量之線迂迴、繞路、模糊或地下化,來生成某種逃逸性的倫理主體化,可行嗎?不知道,但就像格雷伯所說的,在現代流行文化文本中,所有表面上挑戰科層,無視一切規則與規訓的偶像:無論是福爾摩斯、龐德乃至於布魯斯韋恩,其實都沒真正挑戰這個鞏固不平等的暴力/科層結構。
11. 因此我們也就不意外最純正的老派自由主義者,當代最硬頸的右派旗手之一區克夏(Michael Oakeshott),把離開自然狀態的人,比喻成終於學會好好打牌的人,有了起手無回的遊戲規則,我們才終於馴化可怕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爭戰」。Michael Oakeshott, 2008.“A reminder from Leviathan,” in The Vocabulary of Modern European State, p.40.
12. 關於這個主題,可參見Raffaele Laudani, 2013. Disobedience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A Genealogy. 特別是他在導言中對於「黜憲力」(destituent power)的討論。
13. David Graeber, 2004. “Toward a theory of imaginary counterpower,” in 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p.31.
14. David Graeber, 2004. “Blowing up walls,” in 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p.45.
15. 必須強調,對於科層與官僚,左派絕非束手無策,一如曼德爾(Ernest Mandel)的主張,「要削弱官僚的規模與比重,必須在政治生活中開拓出直接民主的重要影響場域」,Ernest Mandel, 1992. Power and Money: A Marxist Theory of Bureaucracy, p.201.
書籍資訊
書名:《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作者: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出版:商周
日期:2016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