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他來說一定像場惡夢。他仍然身處在椰子殼下,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什麼都看不順眼。」
類似的話,對雙方都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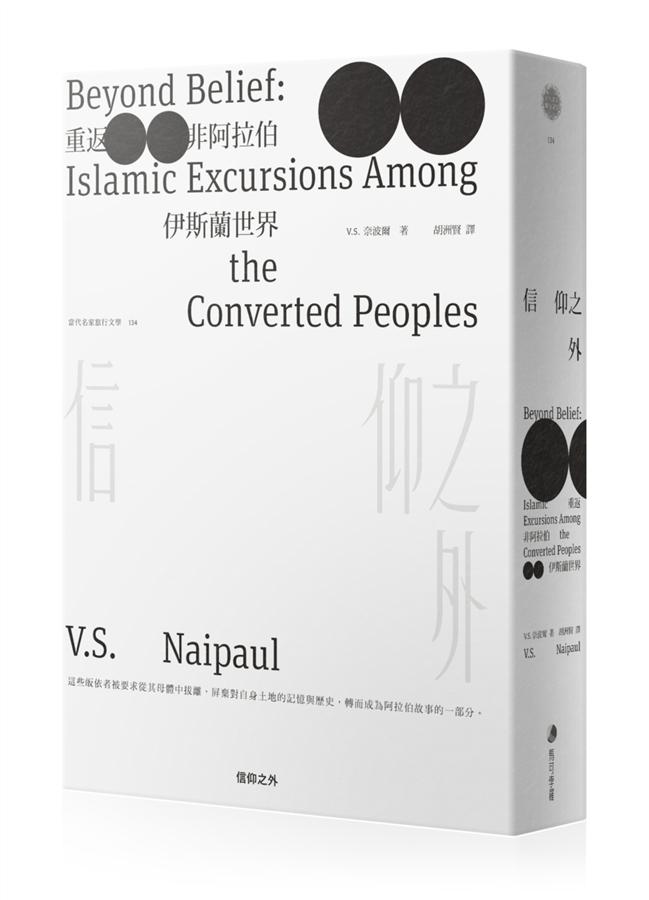
文|V. S. 奈波爾
譯|胡洲賢
娜荻莎的父親出生在一九四○年前後,是個鄉下的馬來村民。娜荻莎從來沒有找過父親的村子,對父親的背景也從來沒產生過興趣。她的家庭再平凡不過,娜荻莎也不認為自己該去尋根。她認定自己的家應該是「農家或諸如此類的家庭」,深信自己的家應該是在田中的木屋裡,廚房就蓋在屋子後頭,家裡不會有書。
但打從小時候開始,教育對娜荻莎的父親就很重要。某個頗受尊敬的長者曾經告訴他,也或許是聽人家說的,總之,他知道對他這種男孩來說,教育是唯一的出路。他很聰明,也很努力念書,最後他得到獎學金,可以到瓜拉江沙著名的馬來學院去就讀。
在瓜拉江沙,他遇見一個女孩,日後便成為娜荻莎的母親。有天,他看到與一位年長女伴走出來的她,當下就被深深吸引。要打聽出她是誰以及家住何處並不難,學院裡的男生對瓜拉江沙的女孩們瞭如指掌。娜荻莎的父親開始和這個女孩通信,女孩也和學院裡其他的男生通信。在瓜拉江沙,這種男孩和女孩間的友誼是被允許的,只不過不能自由的碰面。
女孩和祖母一起住在瓜拉江沙,父親在吉隆坡警界服務。她來自一個沒落的舊式家庭,家中曾經擁有過大片土地,可惜沒有好好經營,結果土地一點一點的流失。賭博吞噬了土地,那是她家家族的惡習。每次齋戒月之後,她們全家就會聚在一起,有時還邀一些朋友玩上兩天兩夜的撲克牌。在娜荻莎的成長過程中,還以為這種事再天經地義不過,認為這是齋戒月之後各地的人都會做的事。
娜荻莎說:「他們很頹廢不振,並且以為可以永遠這樣下去。他們沒受教育,這就是問題所在。在我那個時代,有錢人根本不讀書。」
娜荻莎的話,讓我心生共鳴。她對馬來西亞的評論,同樣適用於一九四○年代以前我所成長的千里達。那時的有錢人和當地白人,一般而言都不讀書,那算是他們的特權之一。他們不需要讀書。殖民農業社會需要的技藝不多,並不要求人們特別有效率或努力或優秀。
娜荻莎說:「回想起殖民時代的歲月,我還以為馬來人就只是到處閒逛聚賭,不做任何有建設性的正事。錢讓別人去賺,像是華人開錫礦場,以及通常是由英國人開的橡膠場。那時候,我以為這是天經地義的。華人和英國人是殖民地的主人,馬來人根本不事生產。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成為公務員或學者,但那得努力工作,所以他們寧可選擇容易的出路。他們對其他的事情一無所知,是標準的『椰殼族』。」
娜荻莎的父親卻必須在馬來學院努力求學,因為這是他唯一的出路。像娜荻莎母親這樣的女孩,就沒有這種需要。有她那種背景的女孩如果不想上學,就可以不上;娜荻莎的母親就幾乎沒上過學,她只要能讀能寫,就夠了。但她並不認為自己沒有受過教育。而且說實在的,事實上,家裡也給了她另一種更獨特的訓練,就是娜荻莎稱之為舊式美德的忠誠訓練。她必須學會如何在眾人面前應對進退:學習不張狂、不顯露感情。最後她成為受訓完整的人;娜荻莎則認為母親是個舊式的跋扈人物。
其實在她和娜荻莎的父親通信時,家中的金錢便大筆流失。當土地逐漸賣掉,金錢逐漸流失後,這個一度很有錢的人家就沒有任何條件在瓜拉江沙待下去了;他們幾乎就和鄉下人一樣,移居到城鎮。等時候到了,一九五八年那個女孩十八歲時,就離開祖母和兩個姑姑,到吉隆坡去和當時已當上高級警官的父親住在一起。
在首都,她有了更多自由,而且首度可以和娜荻莎的父親光明正大見面。他們之間一定達成了某種協議,因為娜荻莎的父親負岌歐洲念書,當他回來時,女孩依然等著他,兩人便決定結婚。女孩的家人雖勉強同意了,卻不喜歡這樁婚事。女方家庭雖然已經沒有什麼錢,卻還有名望,而且女孩的父親現在在警界地位頗高。而儘管娜荻莎的父親在馬來學院念過書,也在國外取得文憑,但看在他們眼裡,仍舊烙印著「鄉下孩子」這個汙名。
娜荻莎在成長過程中一直知道父親是鄉下孩子,她母親則出身另外一個世界,兩個人根本門不當戶不對,但娜荻莎認為雙親最後還是達到了平衡。她父親沉默寡言,這點可能也有幫助。娜荻莎記得,有一次父母爆發口角,起因是父親告訴母親說,她父母從來就看不起他。但他說如果她嫁給她應該嫁的那種人,可能一輩子都會困在霹靂翻不了身。
娜荻莎說:「那可能是真話。」
就連娜荻莎自己也覺得奇怪的是,等到她自己想要結婚時,做法居然和母親如出一轍,也嫁了個雄心勃勃的鄉下男孩。
母親警告她:「你在重蹈我的覆轍。」
娜荻莎在吉隆坡一家證券交易所上班(馬來西亞已經轉型),那男孩或稱年輕人,跟她是同一間辦公室的同事。他長相並不英俊,但娜荻莎本來就不喜歡長得好看的男人。她父親也不英俊,她覺得那在潛意識中一定對自己產生了影響。女人漂亮無妨,男人生就一張好看的臉可就不妙。
這個年輕人深深吸引住她,因為他野心勃勃,但並非癡心妄想,而是相當務實,也很會打算。譬如他會說:「這傢伙明年就要離職了,所以我接替他職位的機會很大。」他知道自己的競爭對手是誰,所以會老早就想好自己的策略,深謀遠慮,非常冷靜。
娜荻莎說:「我自己沒有什麼方向,但我想他會接手那個職位,最後我或許也能成點事。」
我問娜荻莎:「除了野心之外,難道他沒為其他吸引你的地方嗎?」
「他喜歡好衣服。」
男孩的鄉下背景倒是不會困擾娜荻莎,她認為他很怡然自得。但她不喜歡的是他的政治立場。他支持政府和馬來執政黨,因為他認為政府為像他那樣的人做了許多事。當時法官們正受到政府的攻擊,娜荻莎為此十分擔心。
年輕人說:「我不在乎這點。人們真正在乎的是錢、能吃下肚的食物、房子和庇護等等。」
娜荻莎辯不過他,但她認為自己有好的成長環境,而他沒有,如果自己還責怪他,那就錯了。她也知道他對討論觀念上的事情不感興趣,他比較感興趣的是實際的事物。後來這一切都讓她不舒服。但儘管有這些疑慮,她當時還是決定嫁給率直的他,視他為新馬來人、新楷模,所以他們就訂婚了。
「我真的認為自己當時想要結婚。所有的朋友都結婚了,我認為就該如此。現在就該輪到我結婚。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有一天,未婚夫隨口跟她說想帶她到村子裡去見他祖母,並說他父母週末也會過去。娜荻莎之前就在吉隆坡見過他父母幾次。他們很和藹可親,但娜荻莎並沒有特別喜歡他們。雖然受過教育,在吉隆坡住了三十年,但未來的公婆談吐十分稀鬆平常,聊的都是最無所事事的閒扯,絕非娜荻莎會選擇的那種公婆。但娜荻莎當時最主要的需求就是結婚,她覺得生為女人,婚非結不可。她認為生為女人,唯有有個丈夫在身旁,才有前途可言。後來她離了婚,觀念也就跟著改變了。
村子在森美蘭。那裡有條公路,離開公路後就是一條小路,越走越像鄉間小道,也越來越泥濘,讓娜荻莎不禁有深入內地之感。這裡比吉隆坡潮濕,濕氣更重,住屋也越來越簡陋。她看到這一切,也深諳其意,但並沒有被嚇到退縮。此情此景有點熟悉,就像她想像中父親的出身地。正因為這樣的關係,以致她所看所感是一套,所言所行又是另一套。
他家就座落在村子裡很一般的地方,沒有車道。未婚夫的父母早就等候多時,他們也是從吉隆坡開車過來的,汽車在草地上留下泥濘的痕跡。那是當地常見的村子,但房屋本身儘管一部分如傳統的村子樣式架在柱子上,卻不是傳統的鄉下房子,而是經過翻新和增建,而且沒有竹編的牆壁。娜荻莎看到屋子前面有幾隻雞,隨後又看見更多的雞在房屋較老舊的部分底下奔跑。她會注意這些雞,是因為在吉隆坡時,她並不常看到雞在房屋四周奔跑。
她告訴未婚夫:「啊,她在養雞啊。」「她」就是他祖母。
他說:「她喜歡剛下的蛋,味道比較好。」
這幾句話說錯了,聽起來像是在辯護。她認為他話說多了,他實在沒必要說明蛋的味道。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他很不自在。這瞬間一閃即過,她把這感受推到心底深處,不再去想。
這頓午餐共有十個人一起吃,兩個沒出嫁的姑姑在旁服侍,被當成了僕人。家人認為她們理當照顧高齡祖母。娜荻莎想著,祖母就和她孫子一樣醜,不過因為祖母滿臉皺紋,所以到底有多醜,誰也看不出來。吃中飯時她話不多,也無此需要。她是女家長,家人都唯她馬首是瞻。娜荻莎心想,這是森美蘭人的生活方式:這裡的人都是從蘇門答臘的巴東移民過來的,把母系社會的風俗也一起帶了過來。身為未婚妻,娜荻莎並不需多言,只要靜靜地坐著,露出害羞狀即可。所以說實在,午餐倒是吃得挺自在。牆壁上掛著許多張小小的照片,訴說著家裡孩子不同的階段。
在一起吃午餐的某位叔叔是執政黨馬來黨的黨員,參與地方政治。他在餐桌上帶頭談論一些關乎地方事務的政治話題,娜荻莎開始對馬來運動有些新的概念。過去她一向把馬來運動視為理所當然,但現在她開始瞭解未婚夫如何看待馬來運動,她開始瞭解——整體而言:房屋、增建、輕鬆的政治話題、普遍的信心等等——自己正置身於一群感受到世界已經在具體改變的人當中。他們目睹美好的事情在村子、在他們家裡,以及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發生,因而認為自己的地位已經大大提升。
娜荻莎說:「從前你到吉隆坡會看到一些俱樂部、商店等。唯一住在那個世界的馬來人不是皇親,就是國戚。我們覺得這是我們的土地,卻被他們接收了。」所謂的「他們」,指的是華人。「在這個家庭裡,我覺得自己終於瞭解,為什麼政治在馬來人的生活中舉足輕重。在辦公室發生爭執時,我談的是概念,而他談的是具體事物,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她感受特別深的是餐桌上的人都很樂觀。一個家庭表現出這樣的樂觀,對她而言十分新鮮。她還發現對於那個家庭,未婚夫象徵著成就——他們的成就,馬來人的成就。
我問娜荻莎:「他們是不是也將你視同他的成就之一?」
「我不認為這樣。」
「那讓你當時有點愛他吧?」
「沒有。」
「所以你是在欺騙自己?」
「或許我覺得自己在他們所談論的前途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許!」
飯後發生了一些事,她注意到了,但卻忍住,就像她壓抑對庭院中的雞和談論新鮮雞蛋味道時的感受一樣。
「我們到客廳去。餐廳位在房屋老舊架高的地方,客廳則是在新的這邊,必須走下三級階梯,卻反而象徵他們的向上提升。祖母示意我未婚夫到她身邊去,我還以為他是要坐在她旁邊的椅子上,結果他卻坐在她腳邊的地毯上。那裡有塊地毯。一切都是新的。餐廳有塊蘆葦或竹編蓆子,我不確定是哪一種。席地而坐這件事引起我的注意,但那時我只想到那可能是森美蘭的文化。眾所皆知,他們非常有部族觀念。我不想談這件事,以防他認為我對這件事不開心,我也認為他的信心足以處理這一切事情。基本上,只要你不在乎,這一切就沒什麼大不了的。」
這次拜訪進行了大約四小時,從正午到下午四點之前。兩個月後,兩人就結婚了。
娜荻莎的母親有她的疑慮。她說:「你在重蹈我的覆轍。」她對女婿並沒有成見,只是不知道娜荻莎要如何適應。她不喜歡女婿的父母,對方則認為娜荻莎和她父母十分勢利且傲慢。他們覺得必須還以顏色,而就在結婚前,雙方即爆發了類似爭吵之事。
馬來西亞人的婚禮習俗源自於印度古習俗。初期階段,雙方家庭必須交換禮物。如果女方家贈送五項禮物,男方家就必須回贈七項;雙方禮物數目一定要相差兩項。都是些象徵性的禮物:糖果和金錢等。娜荻莎的母親希望男方送的禮物之一是金幣,而不要直接送鈔票,理由是為了好看:金幣擺出來總是比鈔票體面。男方的母親卻一口回絕,說她沒時間到銀行去把鈔票換成金幣。
娜荻莎說:「事實上這是非常沒有禮貌的,因為女方希望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反之亦然。人人都得表現得親切體恤。在婚前,你總不想傷害到任何人的情感。按照馬來人的習俗,你就是該讓步,要表現得大方一點。」
但娜荻莎從她朋友的經驗中得知,結婚時,姻親之間幾乎都會起爭執。爭執來自於雙方家庭的競爭,而娜荻莎寧可把不擅於處理金幣事件當成只是爭執的一部分,但她母親的反應比較苛刻,認為這是對方態度惡劣、出身卑微的象徵。
婚後,娜荻莎到過丈夫鄕下的村子六、七趟,但她從來沒有真正喜歡過那裡。村子的生活並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麼簡樸,充滿田園風味,事實上反而充滿了競爭性。娜荻莎第二或第三次到村子時,話題全是鄰居的新車或吉普車:價錢啊,汽車顏色不好看啊,還有「我敢打賭絕對不是他自己出的錢」等等。負責照顧老祖母的兩個單身姑姑也看彼此很不順眼。村子裡很少有單身漢,兩個姑姑現在已經幾乎沒有結婚的機會。一個姑姑比較認命服從,娜荻莎喜歡這一位;另一位姑姑則比較惡毒,周遭人事若不順她的意,就滿懷憤怒。
村子裡對文化毫不感興趣,生活十分膚淺,有的只是宗教。宗教很重要。每天祈禱五次,標示著時間的流逝。清真寺是唯一的社交中心。
娜荻莎認為因為村人抱怨太多,愛發牢騷,又愛相互比較,她先生才會變得那樣野心勃勃,好突破現狀。讓她困惑的是,丈夫並沒有像她那麼注意那些瑣碎之事,他沒有參與,也不會一起蜚短流長,但卻接受這樣的行為。那是村子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他的一部分。而且雖然娜荻莎沒有明說,但畢竟他生命中全部的公事就是他在吉隆坡的證券交易所。
婚後,他們和娜荻莎的父母住在一起。娜荻莎後來回想起來,認為那真是天大的錯誤。她那個雄心勃勃卻被自己的父母慣壞的丈夫,覺得自己頗受壓抑,無從掌控自己的生活。很快的,雙方的怒火就爆發出來。娜荻莎的母親從未針對女婿個人挑剔,女婿也從未當面批評娜荻莎的父母。他只是攻擊他們的生活方式,攻擊他們做的事,攻擊他們喜歡的人。他不喜歡娜荻莎看《Vogue》雜誌,他會說:「你為什麼要看這些垃圾?」身為馬來人新楷模的他,看的可都是管理方面的書籍,諸如《金錢期權》(Money Options)、《樂趣管理》(Fun Management)等一些與股市有關的東西。
「有一天他和客戶一起出去,喝了點酒。再一次的,我不記得我們爭執的內容了,但這次我們誰也不肯退讓,他打我,我就回手;我叫他滾出去,他真的就走了。我們就是那時候開始談離婚,全部透過律師在處裡。之後他始終沒再回來過。」
這時娜荻莎已經有孕在身,所以沒辦法馬上離婚。在伊斯蘭教中,如果妻子有孕,是不准離婚的:嬰兒必須在合法的婚姻中誕生。娜荻莎知道他們有他們的尊嚴,並且可能是存心要讓娜荻莎的日子難過,而她果然也嘗盡苦頭,在進退兩難中生活了三年,既不像結了婚,又離不了婚,想要取得孩子的監護權更會是場硬仗。
(本文為《信仰之外:重返非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世界》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信仰之外:重返非阿拉伯世界的伊斯蘭世界》Beyond Belief: 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s
作者:V. S. 奈波爾(V. S. Naipaul)
出版:馬可孛羅
日期:2016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