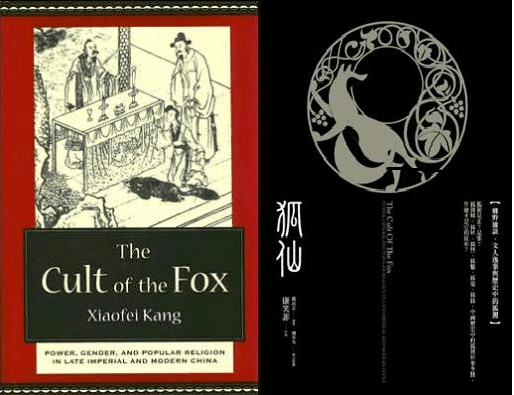
雖說在不同國度的寓言故事中,隨處都能發現狐狸的蹤跡,但是卻很少有一個地方如同古代的中國,在此狐狸的形象是如此複雜多變,一下可以化作色藝雙全的美女,一下又化成飽讀詩書的帥氣書生,或是年高德劭的白髮老者;除此之外,不同時代的文人對於記載、描繪狐仙一事,彷彿無窮盡般樂此不疲,也正因為累積下豐富的筆墨,也才使得清代的兩位大文豪紀昀和蒲松齡,能夠「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為各代以來狐仙形象的演變歷程留下珍貴的記錄。
康笑菲教授在書中自述,兒時不時聽聞母親提起,從前在北京郊外老家後院的那座陰森小廟,總是讓附近的小孩避之唯恐不及,深怕祖母的耳提面命一語成讖,使因為觸怒狐仙可能降至的種種禍害成真。正是從上述的家族回憶作為出發,長大後赴美留學的康教授很早便決心要完成狐仙的研究,本書雖說譯自作者的博士論文,遣詞造句卻毫不生澀,倘若稍微再花點心力,反覆咀嚼書中引用的文言文段落,相信讀者會對印象中冷僻的歷史研究有所改觀。
世有不害人之狐,斷無不害人之鬼
《聊齋誌異》的其中一則故事〈蓮香〉情節如下:有位年輕士子同時與一狐一鬼墜入情網,狐精蓮香自稱為「西家妓女」,女鬼李氏則自稱為「良家女」,兩女別夜而至,日子一久倒也相安無事;然而蓮香很快便發現士子面容日漸憔悴,乃因與女鬼相交所致,儘管再三警示,同時給藥治病,然而士子終究不聽勸而藥石罔效;故事末端,狐精和女鬼在士子的病榻前對質,一開始李氏還惡人先告狀,質疑蓮香士子的病她也有份,反倒被蓮香以此段標題來斥責李氏無視人鬼之別,「陰氣盛也」、「夜夜為之,人且不堪,而況於鬼?」在故事中,除了按照慣例總是有個耳根子軟、懦弱無能的男主角外,兩位女主角非但不是水火不容的情敵關係,反而是在知道彼此的情況下暫且和平共存,最後卻因女鬼的我行我素下,以斷送士子性命收場。
說起狐仙和鬼魂,兩者間確實有不少相似之處:自古以來,祂們均被視為陌生且具危險性的外在威脅,除了會作怪、附身,在文人筆下都曾出現過狐、鬼「祟」(採陰補陽之術)的記載;但就如同蓮香面對李氏強辯義正言詞的回應:「是採補者流,妾非其類」,由此可見自古文人對於狐仙的豐富想像,絕不僅只侷限於陰陽、善惡對立的二分思維,在蒲松齡筆下的蓮香和李氏雖均非人也,但前者表現出的和煦和療癒的能力,便充分展現一股對抗陰損的溫暖力量。即便連乾隆朝的儒家的首席代言人紀昀(字曉嵐,主掌禮部),在編寫《閱微草堂筆記》也反對將狐仙和鬼魂輕易混為一談;甚至到了上世紀進入新中國的1940年代,當年就讀燕京大學社會系的李尉祖,在北京近郊所進行的民族學研究中,所整理村民訪問的結果分析如下:
為了成仙,有仙緣的狐精有三種修煉形式。良善的狐精退隱山林,苦行鍛鍊。邪惡的狐精為祟害人,與人交媾,取其精氣。其他不好不壞
的在人群中惹是生非、挑起爭端,趁機吸取爭鬥者釋出的氣來修煉。
里俗呼狐曰仙家
簡單來說,狐仙雖被歸為陰類,但又被視為介於人鬼之間;雖然被認為具危險性,但又能長時間安穩處在人群中,只要提防發生衝突,人狐之間和平共處並非難事。根據康教授對於北京土話精確地掌握,她認為「狐仙兒」的稱呼是華北居民世代以來,表現出對狐仙既輕蔑又尊敬的矛盾心態:一方面相對於祖先、灶神和各司其職的諸神祭祀,狐仙廟、祭壇則是標準的「淫祠」,始終未有合法承認的位置;然而日常生活上大小事又不時有求於「祂」,於是這種非正式、個人化的親密稱呼很快便在鄉里流傳開來。
自古多數的文人士子,雖然嘴上對民間狐仙崇拜加以痛斥,然而私下卻仍難掩好奇而相約拜訪祭壇,至於一般市井小民少了面子和道德包袱,對於傳聞中有求必應的仙家更是趨之若鶩;下面故事則能充分表現宗教生活在民間的旺盛生命力:從前有間土地神廟,因年久失修而香火寥落,於是有位狐女託夢給村人說:「如果能為我立祀,對你們會有好處。」於是村民靈機一動想說土地神沒伴,何不添置一位夫人像?一段日子下來,仙家越是靈驗,祭祀酬神的活動也越是盛大。某夜,睡在廟簷下的乞丐,在半夢半醒間彷彿聽見爭吵聲;「死泥偶!自從老娘來後,這間破廟才逐漸像個樣,憑甚麼讓你坐我旁邊共享祭祀?」「野狐狸!每天晚上都外出迷人,盡作那些下三濫的勾當。老子寧可忍受挨餓,也不願終年帶這頂綠頭巾。」隨即廟內傳出毆擊打鬥的聲音,隔日村民知情討論後,便將土地神移置殿後,以後凡牲物先祭夫人,而後及土地神,從此相安無事。對於村民來說,在供奉合法的正神時,該拿出的尊敬還是不能少;然而若是需要有效的實際協助或難以啟齒的個人私欲時,各種動物神化成的仙家便成為首選。
無狐魅,不成村
本書的旨趣不只在於鉅細靡遺描述民間信仰和文人筆下的狐仙形象,除此之外,康教授也不時在字裡行間提供讀者,從不同角度理解這些荒誕且不合常理的口耳相傳或文字記載:如果說狐女相伴的豐沛想像,主要是來自文人在禮教束縛下的欲望投射,那麼狐男迷惑凡女的例子,是否與華北、東北地區自古地瘠人貧,迫使窮人家必須販售妻女身體以求溫飽,面對殘酷現實的一種修辭轉化;至於剛到任的地方官和狐仙角力鬥智的傳聞,背後似乎也象徵著長久以來官方和地方勢力的明爭暗鬥。
於是讀者更能體會,在唐朝文人張鷟筆下出現的場景:家家戶戶的百姓多在房中祭祀狐仙,平時人與狐在同張桌上吃飯聊天也極為常見,然而也如同應驗那句俗話――「興一家、敗一家」,狐仙早已習於往來周旋在各家之間;這些世代流傳的記載,除了表面上說明長久以來狐仙信仰的深入人心,此外對於長期封閉的古代中國社會,每位村民、每尊神像和每棟建築都有固定的位置,人們心中自然不時嚮往能有一股「游移」的外在力量,能介入馳騁於道統、官方勢力無法觸及的日常生活中。
書籍資訊:《狐仙》,博雅書屋,2009。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