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發一種新藥的可能性是 3 x10 的62次方之一,原來救人一命比登陸月球還難,
但前人的樂觀和努力,依舊為二十一世紀帶來了先進的醫療科技。

文|唐諾.克希、奧吉.歐格斯
譯|呂奕欣
有一項基本事實,不免令藥物搜獵者耿耿於懷:在一開始時,人們對多數藥物的確切運作方式其實一無所知。新藥究竟如何在人體內完全產生作用,通常需要研究人員花數十年的時間解讀。在許多狀況下,即使歷經好幾世代的研究,我們仍不完全理解,某種藥物如何發揮功效。比方說,到了二○一六年,氣態吸收的手術麻醉劑(例如氟烷)、莫達非尼(modafinil,一種猝睡症的藥物)與利魯唑(riluzole,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用藥)都是藥學上的謎團。對醫師來說,缺乏資訊可能令人不安。但是對藥物獵人來說,卻代表自由。
任何人只要多多留意,都有機會找到可能具備效用的化合物,並將之轉化為有效的藥物,即使不太了解生化機制也無妨。在植物時代,藥物獵人當然對於藥物運作一無所知。探索藥物完全得靠著試誤法。埃爾利希在二十世紀初提出受體理論之前,藥物的運作理論五花八門,有的會誤導人(例如指出藥物會改變細胞的形狀),有的則是荒誕不經(例如深信要治療某種疾病,就要找形態與患病器官類似的植物)。話雖如此,有時即使是最無知的信念,也可能成為某種關鍵發現的催化劑。只要有任何前進的動機,就能激發藥物獵人在崎嶇道路上繼續探索。事實上,第一個驗證藥物確切療效的科學實驗,正是建立在錯誤的假設上。
如今最常冠上「神祕」藥物類別的,應該是抗精神病藥物(psychoactive),亦即精神疾病的用藥。在一九五○年代以前,思覺失調、憂鬱或躁鬱症都無藥可醫,而多數精神醫學界成員認為,這些疾病不可能有藥,因為多數人相信,精神疾病主要是源自於未能解決的童年經驗。這是佛洛伊德的中心理念,他的精神疾病理論(稱為精神分析)在二十世紀初席捲全美。怪的是,佛洛伊德派思想在歐洲幾乎銷聲匿跡,理由卻和在美國備受歡迎的理由一模一樣。早期精神分析者多為猶太人,佛洛伊德也不例外,而希特勒在德國掌權、納粹崛起之際,猶太精神分析者紛紛逃離歐洲,避居美國。精神分析的重鎮從奧地利維也納,變成美國紐約。這就好比教廷從梵蒂岡遷到紐約。
到了一九四○年,美國精神醫學界幾乎全由精神分析派掌權,他們不僅主導大學的學派與醫院,連美國精神醫學學會也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此外,精神分析師也推動了美國精神醫學本質上的深刻變化。在佛洛伊德派人士逃離納粹歐洲之前,美國精神醫學界的精神科醫師以「疏遠派」(alienist)為主流,因為這些精神科醫師在遠離人群聚集處的收容機構,照料嚴重的精神病患者。由於精神療養院遠離了良好的社會,因此精神科醫師也被稱為「alienist」。但佛洛伊德派將精神醫學帶入美國主流,堅稱每個人「多少都有精神病」,只要在精神分析師舒適的辦公室,透過放鬆的療法即可治療。佛洛伊德派把精神醫學從遙遠、孤立的機構,帶進市中心辦公室與郊區住家的舒適沙發上。
精神分析師認為,病人只能透過「對話治療」來治癒,包括以夢境、自由聯想與坦白告解來探索童年經驗。他們相信,沒有任何化學物質可正向改變有精神疾病的人。因此,尋找精神藥物的藥物獵人毫無奧援。在整個一九五○年代,沒有大藥廠有尋找精神用藥的計畫,沒有學界實驗室研究精神用藥。尋找證據、證明用藥可能改善精神病患生理狀態的主流醫院更是屈指可數。仍有些非佛洛伊德學派的疏遠派精神科醫師,在偏遠的精神療養院中處理病況嚴重的思覺失調與自殺病患,他們期盼某天能用藥物來治療病患,但整體醫學界多深信,精神病沒有像灑爾佛散或胰島素這樣的藥物可用。在這種絕望的反藥物環境下,唯一發展精神用藥的希望,就是錯誤假設與好運。然而錯誤假設與好運,向來是藥物搜尋能成功的關鍵要素。
亨利.拉伯里(Henri Laborit, 1914-1995)不是精神科醫師,對精神醫學了解也不多。他是法國海軍的外科醫師,二次大戰時在地中海中隊服役。戰爭期間,他開始尋找新的手術輔助藥物:他推測,若某種藥能讓病人休眠,則可望減少術後休克的風險。拉伯里循著這條思路,推定能降低病人體溫的任何藥物,都可能有助於人工休眠。
拉伯里在突尼西亞的法軍醫院工作時,同事給他一種新的抗組織胺化合物,據信可以降低體溫,這種化合物稱為氯普麻(chlorpromazine,又稱「氯丙嗪」)。他在手術的病人身上試用氯普麻,盼降低術後休克的嚴重性。但拉伯里注意到,在他有機會使用麻醉劑之前,病人的態度會產生戲劇性的心理變化。氯普麻讓他們不在乎即將進行的大手術,等手術完成依然不在乎。拉伯里寫下這份發現:「我請軍隊的精神科醫師,觀察我對幾個緊張、焦慮的地中海地區病人動手術。手術之後,他和我一樣,同意病人相當平靜放鬆。」
事實上,氯普麻並未促成人工休眠,對人體的體溫也沒多大的影響。不過,藥劑對病人產生了意料之外的心理影響,拉伯里對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開始思考,這化合物能不能減輕精神疾病。一九五一年,拉伯里回法國後,說服一位健康的精神科醫師靜脈注射一劑氯普麻,以描述這種藥物的主觀效果。這位被當成白老鼠的精神科醫師一開始說:「沒有值得一提的效果,只有一種無所謂的感覺。」之後,他突然昏倒(氯普麻有降血壓的功用,會使血壓降低)。接下來,醫院的精神科主任禁止了氯普麻實驗。
拉伯里不氣餒,前往另一家醫院,試圖說服精神科醫師對病人使用這種藥物。醫師們拒絕了,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多數精神科醫師認為,控制(而非治療)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唯一方式是使用強烈鎮靜劑—氯普麻不是鎮靜劑。最後,他終於說服一名精神科醫師,測試這會覺得「無所謂」的藥物。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九日,這位精神科醫師靜脈注射氯普麻到病人雅克(Jacques L.)身上。雅克是一位二十四歲的精神病患,非常躁動,有暴力傾向。在注射之後,雅克很快鎮定下來,平靜了數個小時。之後,奇蹟發生了。在每天接受氯普麻注射的三週之後,雅克可正常活動。他甚至能毫無中斷地玩一整局的橋牌—這是過去根本難以想像的。他恢復得很好,醫師覺得驚訝,讓他出院。精神科醫師們目擊了醫學年鑑上前所未見的事:這種藥物完全消除精神病的症狀,讓過去無法控制的暴力病患回歸社群生活。
一九五二年,法國藥廠羅納普朗克(Rhône-Poulenc)公開推出氯普麻,商品名稱為Largactil。隔年,美國史克藥廠(Smith, Kline, and French)則以Thorazine 為商品名來銷售氯普麻,結果一塌糊塗。沒有醫師開這處方,因為多數精神科醫師並不認為藥物能治療精神疾病,連理論上都不可能。美國精神科醫師鄙視氯普麻,認為那隱藏了病人童年的病因,而不是加以治療,有些知名的精神科醫師還嘲弄拉伯里的藥物為「精神病阿斯匹靈」。
史克藥廠訝異極了。他們銷售的可是第一種能確實治療精神病症狀的神奇藥物,但精神科醫師卻不捧場。終於,藥廠想出解決方案。史克藥廠不再設法說服精神科醫師開藥,而是把目標鎖定在州政府,主張公辦精神療養院使用氯普麻,就能讓病人出院,不必永遠收留他們,如此可大幅降低成本,減少政府支出。幾家比較關心盈餘、不願討論深奧精神病哲學的州立精神病患收容機構嘗試了氯普麻。結果正如史克藥廠所稱,除了最病入膏肓的患者之外,其餘患者病情皆出現大幅改善。許多人可以出院,回歸社會。
史克藥廠的營收在接下來十五年翻漲八倍。到一九六四年,在全球有超過五千萬人使用氯普麻,這成為思覺失調患者的第一線用藥。過去患者只能迷失在宛若地牢的公共療養院,如今竟能過著充實的人生。氯普麻的成功,也代表精神分析與佛洛伊德主宰美國精神醫學界的情況即將畫下句點。若可以吞個藥丸,看著症狀消失,又何必年復一年,每個星期坐在精神科醫師的沙發上聊你母親呢?
如今我們所使用的抗精神病藥物(antipsychotic,多用在治療思覺失調),包括奧氮平(olanzapine,商品名「津普速」Zyprexa)、理思必妥(risperidone,商品名「理思必妥」Risperdal)、氯氮平(clozapine,商品名「可致律」Clozaril)都是氯普麻的不同化學版本。氯普麻的臨床應用超過六十年,科學界基本上無法找出更好的方式。然而,氯普麻究竟如何減緩思覺失調的症狀,目前仍不明朗。不過,這並未阻止每家藥廠嘗試仿製氯普麻。
其他藥廠想和羅納普朗克與史克藥廠一樣,找出世界第一種抗精神病的暢銷藥,因此各自集結團隊,合成氯普麻化合物。其中一個很有希望的模仿者是瑞士藥廠嘉基(Geigy),亦即諾華藥廠的前身。嘉基的高層主管找上羅蘭.庫恩(Roland Kuhn, 1912-2005),他是一位瑞士精神科教授,對於尋找新的精神病藥物有著強烈興趣。嘉基給予他類似氯普麻的化合物(公司標示為G 22150),請他在精神病患身上試用。結果這種藥物會產生極難以忍受的副作用,不適合用來治療。因此在一九五四年,庫恩請嘉基公司提供新的化合物。
庫恩和嘉基的藥理學主管相約在蘇黎世的一間飯店會面,這時庫恩看見一張很大的圖表,上面有四十個手繪的化學結構。嘉基公司的主管請庫恩選其中一個。庫恩指向其中一種看起來最類似氯普麻的化合物(編號為G 22355),結果這宛如命運的安排,將使事情有所改變。
庫恩回到醫院後,將G 22355給幾十名精神病患使用,卻發現沒什麼動靜,當然也不像氯普麻那樣能明顯減輕症狀。庫恩原本可能會請嘉基改提供另一種化合物,但他決定嘗試其他做法。庫恩在未告知嘉基的情況下,讓其他憂鬱症患者服用G 22355。
前文提過,第一種抗精神病藥物是幾年前才剛發現,且不是源自於大藥廠的研究計畫,而是一名在突尼西亞的外科醫師設法降低術後休克時使用的。如今,一名瑞士精神科醫師決定忽略他受託的任務,尋找新的抗精神病藥,反倒決定把失敗的抗精神病藥,應用在憂鬱症患者上。為什麼?因為他必須醫治的憂鬱症患者,人數遠超過思覺失調的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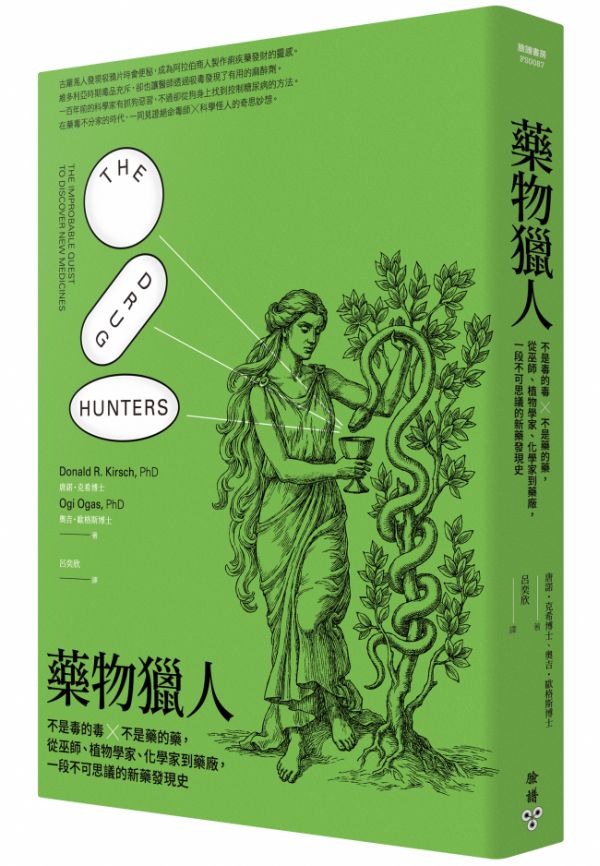
打從久遠以前的前科學時代,早期精神醫學就把瘋狂與憂鬱視為兩種不同情況。瘋狂似乎是因為認知能力出問題,憂鬱症則是情緒出問題。沒有任何醫療或藥學的理由,讓人想到降低精神病患幻覺的化合物種類,可提升憂鬱患者的喜悅感。多數精神科醫師相信,精神錯亂與抑鬱都是情感衝突所造成。但是庫恩私下卻對憂鬱症有不同看法。
庫恩不接受精神分析派的標準看法,不認為憂鬱症是對父母的憤怒受到壓抑。因此,庫恩不採用精神分析的治療方式,而是深信憂鬱是源於某種生物性的腦部失調。既然沒有人知道氯普麻究竟如何產生作用,何不嘗試將氯普麻的仿造品用在憂鬱症患者身上,看看會如何?
於是,庫恩把G 22355 用在三位重鬱者身上。他等了幾個小時就去查看病人,結果沒有動靜。他隔天早上又去查看病人,依然毫無動靜。氯普麻通常在投藥後的幾個小時,甚至幾分鐘內就會產生顯著改善,因此庫恩若放棄測試似乎很合理。但他繼續讓這三名病患使用G 22355,原因為何,恐怕只有庫恩自己知道。終於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月十八日早上,也就是使用這療法後六天,一位稱為寶拉(Paula I.)的女病患告訴護士,她的憂鬱症顯然治好了。
庫恩滿心歡喜地聯絡嘉基公司,宣布G 22355「對憂鬱症有明顯效果。病況明顯改善,病患覺得不那麼疲倦,沉重感受減少,阻力不那麼明顯,情緒好轉」。換言之,庫恩端上銀盤給嘉基,上面放的可能是世上第一個抗憂鬱劑。嘉基的主管是不是開香檳慶祝呢?不。他們壓根兒不在乎憂鬱症。他們想要的是能與氯普麻分庭抗禮的抗精神病藥物。他們要求庫恩停止測試G 22355,並把這化合物交給另一名醫師,明白要求對方只用在精神病患上。
庫恩設法將他的發現傳達給其他科學家知道。一九五七年九月,庫恩受邀到第二屆全球精神醫學大會(World Congress of Psychiatry)上演說,發表關於G 22355對憂鬱症患者的效果。在場的聽眾僅區區十幾人,且無人提問。與會的美國精神科醫師法蘭克.艾德(Frank Ayd)是虔誠天主教徒,他後來說:「庫恩的話就像當年的耶穌一樣,有權威地位的人根本不理不睬。不知當時在場的人士明不明白,我們聽到的藥物將對情緒失調的治療帶來革命性變化。」
看來G 22355 就要被扔進歷史的垃圾桶了。但是,嘉基公司一名深具影響力的股東羅伯.百靈佳(Robert Boehringer, 1884-1974)恰好詢問昆恩,能不能看看罹患憂鬱症的妻子。庫恩立刻推薦G 22355,於是百靈佳太太康復了。百靈佳看見妻子有明顯的改善,遂遊說嘉基公司銷售這藥品。一九五八年,嘉基終於開始販售G 22355,取名為伊米胺(imipramine)。
不久後,諸多抗憂鬱劑問世,而伊米胺正是這些藥物的原型藥。時至今日,每一種知名的抗憂鬱藥的基本機轉仍與伊米胺一樣,都是影響神經傳導物質「血清素」。就連百憂解(Prozac)也是伊米胺的改版。雖然我們仍不明白抗精神病或抗憂鬱藥如何改善患者病情,但我們對於其生理機轉已有基本的認知。氯普麻與伊米胺就像亂槍打鳥,而不是瞄準單一精確目標的狙擊槍。氯普麻至少會啟動十幾種不同的神經受體,多數和思覺失調症無關。根據推測,氯普麻能對抗思覺失調,是因為阻斷了兩三種多巴胺受體。但若只是如此,這藥物會產生難以忍受的副作用,包括嚴重的不自主動作,也就是運動困難(dyskinesia)。不過氯普麻與許多衍生的抗思覺失調用藥,也會阻斷血清素受體,恰好減輕多巴胺受體被阻斷時所造成的運動困難。這種奇特的交互作用,讓氯普麻藥物能治療思覺失調,同時不產生令人難以忍受的副作用。
伊米胺也會命中腦部許多不同的受體,其中多數和憂鬱症無關,還有幾種會造成不良副作用。但伊米胺(以及每一種已知的抗憂鬱劑)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血清素再吸收幫浦(serotonin reuptake pump)。血清素再吸收幫浦可控制神經突觸中血清素神經傳導物的量。(百憂解與類似藥就是「選擇性血清回收抑制劑」(SSRI)。)為什麼增加大腦的血清素可以降低憂鬱?至今仍不得而知。
為什麼兩種化學上很類似的化合物,會分別對很不同的精神失調症狀有明顯療效?神經傳導物的類別很多,包括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與多巴胺,這些物質稱為生物胺(biogenic amine),因為它們都有一種特殊的化學結構「乙胺」(ethylamine)。這表示含有乙胺次結構的其他分子(即使是並非人體自然生成的合成分子),都有很高的機率會對大腦產生某種效果,或是同時啟動不同區域,產生多重效果。這些可啟動身體多重目標的特殊化學結構(例如乙胺),即是科學家所稱的「優勢結構」。
氯普麻與伊米胺都有乙胺結構,因此對腦部的神經受體有很廣泛多元的效果。拉伯里與庫恩靠著純然的意外,獲得能引發腦部多種變化的藥物,而且很幸運,這些變化是利大於弊。
古老諺語說:「好運比聰明重要」。藥物獵人若能兼具好運與聰明,成功機率就最大──拉伯里與庫恩正是如此。
書籍資訊
書名:《藥物獵人:不是毒的毒 x 不是藥的藥,從巫師、植物學家、化學家到藥廠,一段不可思議的新藥發現史》 THE DRUG HUNTERS:The Improbable Quest to Discover New Medicines
作者:唐諾.克希(Donald R. Kirsch)、奧吉.歐格斯(Ogi Ogas)
出版:臉譜
日期:2018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