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漢娜鄂蘭》這部電影在台灣上映之前,就從一些住在國外的朋友那兒聽聞他們的評價,沒什麼人覺得這是部好看的電影。的確,看完之後我不能不認同,對於習慣電影至少要給予一點美學或文學上愉悅感的觀眾來說,我的期待落空了。至於這部電影有沒有給予人們思想上新的啟發,我認為至少在考據這方面的確下過苦心,有助於非學術圈的觀眾了解鄂蘭。
漢娜鄂蘭正如同片商行銷所言,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就我個人的觀點,鄂蘭的特別之處在於,她堂堂正正的迎擊人類思考上的困境,而並沒有花費太多時間岔出去討論性別、種族之類讓事情變得複雜的議題。年輕時期,鄂蘭曾與德國另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學家海德格建立一種類似師生戀的關係,而海德格日後一度公開支持納粹。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鄂蘭因為猶太人的身分輾轉流亡,最後終於前往美國,並與海因里希·布呂赫(Heinrich Blücher)結為連理。

以上種種曲折的人生經歷,若在好萊塢編劇手中,絕對足以製作成盪氣迴腸的感人年度歷史言情大戲。其中涉及諸多偉大名字,簡直就是20世紀哲學界的全明星賽。但是德國導演瑪格麗特‧馮‧卓塔(Margarethe von Trotta)並沒有這樣做,她僅僅擷取了鄂蘭一生中短短的一部分,也就是已步入中年的1961年前後,呈現鄂蘭如何自告奮勇親身旁聽耶路撒冷大審,如何寫下備受爭議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因而承受來自猶太知識界的巨大壓力。在主線故事中,偶然穿插鄂蘭與海德格的交談回憶,但不是為了滿足觀眾偷窺學術泰斗私人生活的惡趣味,而是為了對照兩人是如何同樣經歷了可能太過度的道德指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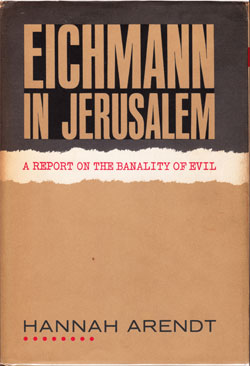
一切爭議的導火線,發生在1961年的耶路撒冷大審,在很多意義上都是有問題的審判。耶路撒冷大審的存在是為了審判一名漏網之魚戰犯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此人負責研擬運送猶太人去集中營跟處決的對策。他並不是下令屠殺猶太人的人,但他的存在確實讓屠殺得以順利進行。耶路撒冷大審明顯的程序問題在於,艾希曼原本逃亡多年,是被以色列特務跨國「綁架」到以色列去的。此外,審判艾希曼的是以色列法院,相較於1945年的紐倫堡大審,戰勝國至少組了一個國際軍事法庭來審理戰犯,艾希曼並沒有得到公平的待遇。
艾希曼在1962年被處絞刑。就結論而言,鄂蘭並不反對艾希曼有罪,但是1963年的書中,她提出了「邪惡的平庸」的概念,提醒世人,在她眼中艾希曼並不是魔鬼──事實上,他根本不配做個魔鬼。艾希曼是個可憐兮兮、流著鼻涕的老頭,他辯解自己並不仇恨猶太人,只是「依法行事」而已。與康德曾提出的根本之惡(radical evil)不同,鄂蘭認為此人的惡行沒有伴隨著什麼激情或信念,因此只能稱得上是渾渾噩噩的惡。
對於鄂蘭的這項觀察,當時的猶太社群感到群情激憤。好幾個鄂蘭的良師益友都因此與她絕交,電影忠實的呈現出了此一衝突。無論鄂蘭對於艾希曼的觀察是對是錯,不是猶太人的觀眾實在很難體會,何以這些明顯是出於理性思考的主張會如此激怒這群戰爭的倖存者。何以鄂蘭敬愛的老師,會在病榻上別過頭去不願原諒她?鄂蘭在書中提到,部分猶太人菁英為了減低傷亡而配合納粹屠殺,對於猶太人的死同樣負有責任。這樣的敘述在二戰結束後過了十六年,依然太過赤裸,足以傷害猶太人的心。

當一項來自政治與時勢的傷害慢慢但持續的發生,就後見之明的觀點來看,倖存者在過程中為了活下去所做的讓步,難免顯得自私且愚蠢。但若覺得人類總是可以透過努力來做出最高尚、最正確的道德判斷,恐怕也是不切實際的。
我曾看過這樣一句話:「像這種小奸小惡之人,連下地獄的資格都沒有。」我們經常想像罪惡是容易辨識跟判斷的,因為既然名之為罪惡,那麼想必是人神共憤,但是這樣的惡並不常見。為惡之人不見得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是制裁惡人的人卻為了自己還想當好人的緣故,必須相信對方真的罪大惡極,否則師出無名。這是多麼沈重的負荷,跟多麼無聊的遊戲?「平庸的惡」這個概念,其實究極而言,有機會能夠解除「好人」的負荷,但好人卻無法輕易接受它,我想這或許就是好人/壞人遊戲中最微妙之處吧。
電影資訊
《漢娜鄂蘭:真理無懼》(Hannah Arendt)- Margarethe von Trotta,2013
書籍資訊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玉山社,2013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