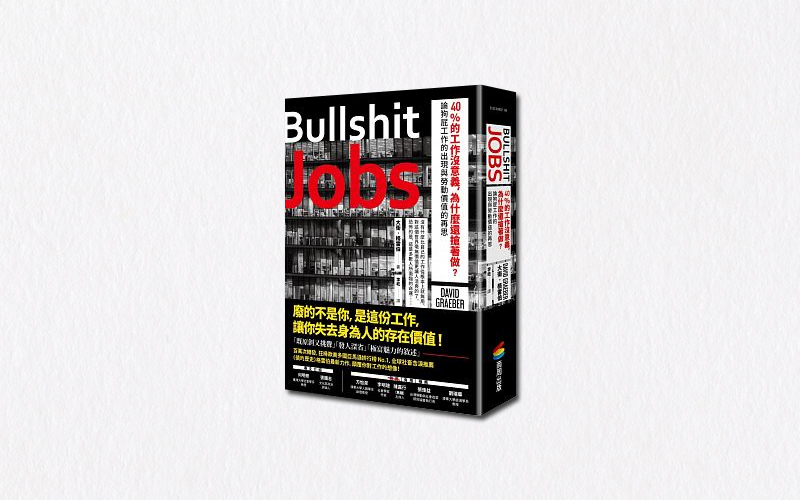
文|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譯|蕭育和
1930年,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經預言,到了世紀末,在像是英國與美國這些國家,科技的進步足以實現每週工作十五小時的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凱因斯是對的,僅就科技面相來說,我們完全辦的到。然而,這卻沒有發生,甚至可以說,科技已經被完全收編,用來搞出各種花招,讓我們做更多的勞動,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就得創造出一些實際上毫無意義可言的工作。特別是在歐洲與北美,有一大批人把他們的職場生涯虛擲在執行一些,他們私下相信根本完全不需要做的工作上。這種情形所產生的道德與精神傷害非常嚴重,堪稱是一道我們集體精神的傷疤,然而卻幾乎沒有人討論過。
為什麼凱因斯所許諾的──直到60年代仍被熱切期待──烏托邦,從來都沒有成真呢?今天的標準解答是,凱因斯沒有考慮到大幅增長的消費至上現象,在更少的工作時數,與更多的玩樂享樂之間,我們蜂擁選擇了後者。這也許是個不錯的道德寓言,但只要深思片刻,就會知道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是的,20年代以後,我們看到的是,層出不窮的各種令人眼花撩亂的新工作與產業型態,但這些工作卻跟壽司、iPhone與超潮運動鞋的生產與分配,卻少有任何關係。
確切來說,這些新的工作是什麼呢?美國最近一份比較1910年與2000年的就業報告,給了我們一個清楚的圖像(而且我要指出,英國的狀況也完全呼應了這個現象)。在上個世紀中,受雇為家務勞動、工業與農業部門的勞動者數量劇烈下跌,與此同時,「專業人員、經理人、文職人員、銷售與服務勞動者」卻翻倍成長,「從總就業四分之一,成長到四分之三」。換句話說,一如預言,大量的生產性工作已經被「自動化」消失掉(即便計入全球性的產業勞動者,包括印度與中國的勞苦大眾,這些勞動者也仍然沒有在世界人口的百分比中佔據過去所佔那麼大的比例)。
但我們卻沒有迎來全人類的解放,讓人人都可以追尋自己的目標、享樂、願景與理念,工作時數也大幅減少的時代。我們所看到的,不僅僅是跟行政部門一樣,各種「服務」部門的虛胖,還包括公司法務、學院及公衛行政、人力資源與公共關係等等部門,前所未有的膨脹,甚至更創造出一些全新產業:像是金融服務與電話行銷。但這些數字,無法反映這些人所做的這些工作,其實是為了為企業提供行政、技術與安全上的支援,我提議把這些都叫做「狗屁工作」。就此來說,之所以會存在這麼多的輔助性產業(狗狗洗澡服務,或者不打烊披薩外送),正是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得在其他的事情上,花上大量時間勞動工作。
這狀況就好像是,有些人在那裡搞出一堆無意義的工作,就只為了要讓我們鎮日勞動。而這就是謎之所在,在資本主義中,這確切來說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在蘇聯那種就業同時被當作是權利與神聖責任,死氣沉沉沒有效率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整個體系必須要充填許多無意義的勞動(這就是為什麼,在蘇聯的百貨公司,得動用三個店員賣一塊肉的原因),而這就是市場競爭所要根治的問題,最起碼,根據經濟學理論,一家追求利潤的公司最不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把錢掏出來聘用一些他們並不真的需要的員工。不過,不管怎樣,這一切還是發生了。

雖然企業很可能會狠搞裁員,但解雇冗員與組織瘦身,卻始終落在確實在生產、運作、處理與搞定事情的那一層人身上。彷彿某種神秘力量在作用,沒有人可以解釋,為什麼到了最後,辦公室的文書工作看來反而是在擴張,越來越多員工發現自己跟過去蘇聯的勞工沒有什麼兩樣,每週得在文書作業耗上40到50小時的時間,但實際上就像凱因斯預言的那樣,差不多只花了15小時工作,其他的時間都花在組織或者出席激勵講座,更新他們的臉書檔案,或者下載套裝電視影集。
答案很清楚無關乎經濟:這是個道德與政治問題。宰制的階級很清楚,一群手上有自由時間,幸福快樂又有生產力的人,是致命的危險(想想快要接近這一切的60年代,開始發生了什麼事)。另一方面,「工作就其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價值」,以及「任何不願將清醒時間泰半奉獻給某種高壓工作紀律的人,活該什麼都得不到」的想法,對他們來說也非常實用。
在反思英國學術部門中,行政責任明顯毫無止境的增長時,我想出了一個地獄的可能光景,地獄裡聚集了一大群人,他們把大部分時間與精力消耗在他們不喜歡,而且也並不特別擅長的工作上面。這群人之所以被雇用的原因,據說是因為他們都是優秀的家具木匠,但接著他們發現他們被期待要做的,卻是花上很大一部分的時間炸魚,而這個工作也沒有真的需要做完,真的需要炸的魚其實很有限。但不知怎的,這些人開始執著於有些同事可能沒有花更多的時間在製造家具上,而且也沒有公平分擔炸魚責任,可是用不了多久,整個工作室裡面又成山堆滿了被炸壞過熟的魚,而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
我認為這就是對我們目前經濟的動態,一個相當精確的描述。
對於這樣的說法,我知道現在一定會馬上遇到反駁:你是哪位?憑什麼說怎樣的工作真的有必要?什麼才是必要的工作?真的有需要你一個人類學教授這種工作嗎?(也確實有很多小報讀者認為,如果我這種工作的存在不是在浪費社會資源,那什麼才是?)在某種程度上,這也不能說錯,社會的價值本來就沒有客觀的衡量標準。
我不會那麼放肆,對一個深信自己的工作對於這個世界有意義非凡貢獻的人說:「其實你的工作真的沒有意義。」但對於那些自己也相信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的人呢?不久以前,我跟一個從十二歲起就沒再見面的朋友重新取得聯繫。我很驚訝地發現,在這段時間裡,他先是成了一個詩人,接著成了獨立樂團的主唱,我在廣播中聽過他一些歌,但完全沒想到主唱就是我認識的人。這樣一個才華洋溢,創意無限的人,他的作品毫無疑問為世界各地的人們的生活增色不少。然而,在幾張專輯賣不好之後,公司不再續約,他苦於債務,還有一個剛出生的女兒要養,最後,他選擇了「跟許許多多對人生毫無方向的人一樣的預設選擇」:法學院。現在的他,是紐約一家知名公司的企業律師。他是第一個向我坦承,他的工作完全沒意義,對世界毫無貢獻,而且照他自己的看法,這種工作根本不應該存在。

在這裡人們可能會有很多問題,就從這個開始:我們社會似乎對於天才詩人與音樂家,只有極端有限的需求,但卻很明顯對公司法的專家,有著無限的需求,這說明什麼?答案是,當有1%人口控制了絕大部分的可支配財富時,他們叫做「市場」的東西,就會反映他們認為有用或重要的東西,其他人怎麼想不重要。不過,更重要的是,這表明大部分身居這些工作的人,最後都會意識到這件事情。事實上,我還真的無法肯定,有遇過什麼企業法務,是沒把自己的工作當狗屁的。上述的所有新產業也是同樣的狀況,假如你在派對遇到一整群高薪的「專業人士」,並且坦承你做的事是被認為還蠻有趣的工作時(比如說,人類學家),他們其實會完全避免談論他們的工作,再幾杯黃湯下肚,他們就會開始長篇大論他們的工作有多麼沒意義又愚蠢。
這是非常嚴重的心理暴力。一個內心覺得自己的工作根本不應該存在的人,是要如何能開始談起勞動尊嚴呢?又要如何能創造出一種深刻的憤怒與怨恨感呢?然而這就是我們社會天才的地方,它的宰制者想出了一個辦法,來確保這種憤怒會精確地指向那些確實在做有意義事情的人身上,像是上面提到的炸魚例子一樣。比方說,在我們的社會中,似乎有一個一般性的法則,一個人的工作越是對其他人有益,他拿到的報酬就越少。除開少數被刻意吹捧的例外以外(像是醫生),這個法則驚人地通用。
再次強調,也許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衡量標準,但一個簡單的辦法,是有意識地問:假如有一整個階層的人完全消失,會發生什麼事?隨便說說,像是護士、收垃圾的人或者技工,假如這些人一縷輕煙般全部消失,這後果很明顯是立即而且災難性的。一個沒有教師或者碼頭工人的世界也會馬上遇到麻煩,如果再也沒有科幻小說家,或者Ska音樂家,這個世界很明顯會變得無聊。但是如果所有的私募基金CEO、議案說客、公共關係研究者、精算師、電話銷售員、法警與法務顧問也同樣消失的話,人類會蒙受什麼苦難呢?這就不很清楚了(有些人懷疑,這樣世界可能會更好)。
更讓人錯亂的是,一種流行的說法是,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子啊。這是右翼民粹論者一個秘密的強項,當小報聲嘶力竭咒罵地鐵工人,只因他們為了合約糾紛而罷工癱瘓倫敦時,你就會看到這個強項。地鐵工人能夠癱瘓倫敦這個事實,表明他們的勞動確確實實是必要的,而這似乎也正是惱人的地方。在共和黨人成功動員出憤恨學校教師,或者汽車工人的能量,只因他們據說浮報工資與福利(值得一提的是,不是針對真正搞出問題的學校管理階層與汽車工廠經理人)的美國,右派這個強項就更清楚了。這就好像是他們被告知「你要教小孩!要製造汽車!你都有真正的工作了!都已經這樣子了你居然還好意思也要求中產階級的年金跟醫療服務?」
假如有人設計了一個跟金融資本的力量完全搭配的勞動體制,就很難看到他們是如何把工作做好。有生產力,真正的勞動者不斷地被無情輾壓與剝削,剩下來的,可以區分成幾無例外被恐嚇與痛斥的失業者階層,以及一個被付錢聘來,但基本上什麼事也不幹的更大階層,他們被擺到一個旨在讓他們更認同統治階級(經理人或行政人員等等,尤其是那些金融界新神)觀點與感受的位置,同時也助長醞釀了他們對所有具有明顯與無法否認社會價值工作的憤恨。
很顯然,這個體制從來都不是有意識這樣設計的,它來自於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嘗試與錯誤,但這是為什麼儘管我們已經有了科技潛力,還是無法每天只工作三到四個小時的唯一解釋。
書籍資訊
書名:《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論狗屁工作的出現與勞動價值的再思》 BULLSHIT JOBS
作者: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出版:商周
日期:2019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