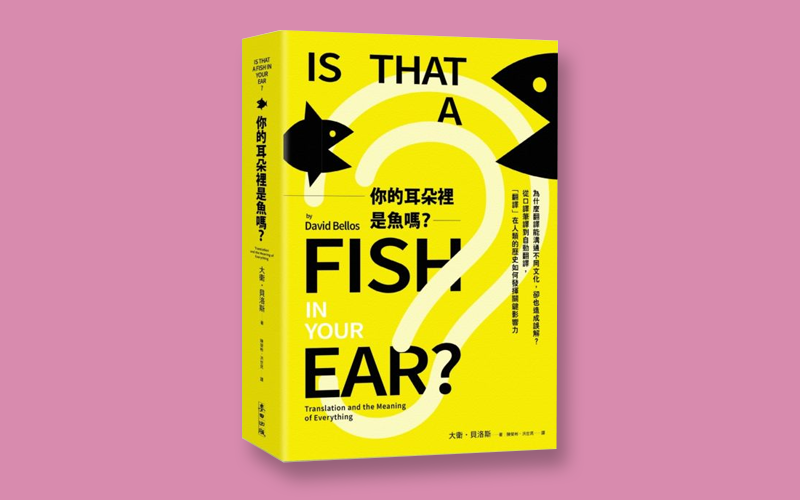
欸,等等,你的耳朵裡是魚嗎?嗯,別動......就我觀察,牠鵝黃色,小小隻的,形狀有點像水蛭......等等,不要緊張,我查查《銀河系漫遊指南》:「巴別魚,很可能是宇宙中最奇異的事物,牠依靠接收宿主之外的腦電波能量維生,並且會轉化成營養,並向宿主排泄出由精神頻率和大腦的神經信號所產生的心靈感應矩陣.......換句話說,如果你耳裡有一條巴別魚,你就能立刻理解以任何形式對你訴說的語言,那些解碼信號就是巴別魚所排泄出的腦電波矩陣......」聽起來很美好,若能在現代社會擁有一隻這脫胎自科幻小說的奇異生物,與外國人接觸的場合不再需要語焉不詳的慌亂手勢、尚失脈絡的孤立語彙,所有意義都能在彼此之間滑順地轉換拋接,因巴別魚替我們略過那神秘轉換過程,我們稱之為翻譯的幽微曲徑。
身兼譯者和研究跨文化溝通的學者,大衛.貝洛斯所著的《你的耳朵裡是魚嗎?》聚焦於翻譯種種細節,從歷史沿革、現象觀察到概念思辨,他旁徵了諸多資料去探究翻譯實際操作時會觸碰到的疑議。畢竟我們都曉得,翻譯不只是單純的意義轉換,更像是兩種島嶼間不得不的接壤迷宮,在相異字句結構、各式文化底蘊和殊異接受程度等變因影響之下左拐右彎,從來無法直線抵達。在書中他提出了幾個懸問,例如:詩是可以被翻譯的嗎?還是有什麼會在轉譯過程失真?在不被告知的情況下,讀者可以知道自己讀的是譯文還是原文嗎?所謂真正好的翻譯,應該如何去定義云者。
以第一個問題為例,翻譯界中有句諺語主張「詩是在翻譯過程中遺落的東西」,作者並不認同,他認為要說丟失,除非你也能了解原詩之中在譯出語呈現的詩意,兩相比較後才能定奪誰優誰劣,否則此話並不成立。更何況詩性即是架構在音意關係之中的概念,不同語言無法構築出全然相同的樣貌,本就無法勉強。回望西方傳統,詩不僅由各個詩人迸發創生,也在義大利文、法文、英文等語言之中遷徙,在「寫詩、譯詩和譯寫詩之間沒有明顯的分野」,在那些翻譯之中也並非直譯,在字句語法中嚴密緊扣,所謂「你不是把法文詩譯成英文,而是譯成詩」,西方詩歌的歷史就等同於翻譯詩歌的歷史。
在論及翻譯的外緣議題方面,他注意文學圖書的翻譯市場,具有文化優勢的語種如英文、法文,會吸引較劣勢者如華文、阿拉伯文的譯入,導致文化輸出入的失衡。在法律方面亦與各式語種的翻譯有關,如法國新政權在1789年所制定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當中的陽性詞「Homme」代表著男性市民,在性別平等思潮逐漸興起後,往後各國對「人權」的翻譯又應當要怎麼處理?歷史也會在某些時刻推動了翻譯進展,像是因應1945的紐倫堡審判,面對英、法和俄控告德國至少涉及四種語言的交叉攻訐,便在法庭中草創了同步口譯制度,完成複雜的語言翻譯中繼網。因此可知翻譯不只純然在話語層面運作,也連帶隱然塑造了外界狀態。

綜觀全書,不難發現當中隱含作者之於翻譯的樂觀期許,基於哲學家卡茨(Jerrold Katz)的可表達原則 (axiom of effability):任何一個人可產生的想法必能以自然語言的句子表達;而能用一種語言表達的事物,必也能用另一種語言呈現,翻譯本質守備範圍極其廣泛,外野界線便等同於語言極限。但多數時間譯文被視為原文附庸,譯文被「是否與原文意義相同」的道德綁架了,對或錯,便直接認定了譯文價值與否。對此作者認為,譬若不同樂手演奏同一首曲會有殊異風格,或多個裝飾音和轉音變奏,譯者同樣也能在某一個框架下「自由」的寫下自己的譯文。
那麼,應該要怎麼樣才算是好的翻譯呢?在彼此話語轉化的縫隙之中有些不肯定的空間,資訊(這句話本身的意思)與效力(要帶給讀者的意義)在此逸出,如無嗅氣體般難以捉摸與定義,這是在原句說出口時必然消散的。於是譯者便要開始補綴字句,斟酌運用形式對等或動態對等致力回復原句,前者意指譯文順序嚴密對應著原文的語法與字彙;後者則指採用譯入語社會中可替代的其他同義敘事,務求資訊與效力就算已失去原初外表,內在核心依然能無失真抵達此岸。藉著拆分句構與意義之間的環節,譯者工作像是先拆開一輛進口車,觀察裡頭的零件陳設與運行方式(資訊),考量最後成車外貌以及消費者的觀感(效力),最後再將它用不同材質(語言)重組拼接,過程中也可能遇到零件短缺,這時選擇的替代方案,即是譯者不常為人見之的自由。特別是翻譯文學性書籍,它籠統神秘得難以描出草圖,如此自由更顯得臨淵而懼,從原文消化到再創造譯文,譯者銜接兩端,它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單方向服膺或一味模仿,如作者所言:「譯作不能和原作相比.......譯者要做的是找到作品組成元件的對應,而非對等,寄望、期待那些對應的總和能創作出一部整體而言足以替代原文的新作。」
說了這麼多,回過頭再來探討本質:到底什麼是翻譯?很純粹的,就是將一種語言的意義轉殖成另一種語言,終極目標都是在理解對方,更進一步說是渴望理解,而語言被視為彼此溝通的載具。可在作者戲言為胡謅的後記中,他卻認為史前時期,手勢先於話語出現,手部動作足堪傳遞資運,而話語反倒是器官的寄生使用,其用途也僅限於加強族群特性。換句話說,言語根本上並不是化解屏障的存在,更強烈的目的應當是強調彼此不同,而此不同,被理解成下文提及翻譯的重大前提。
我喜歡最後作者所提的想法,雖然脫胎自《阿凡達》有點難以理解,其言翻譯這件事需要滿足兩個大前提:一是我們都一樣,能夠理解我們所共同擁有的情感、資訊以及感受,你所觸碰到的幽微心境,也曾讓地球另一隅的心靈無從言喻;再者是,基於如此前提,我們並不一樣,受限於彼此思考的語言,人們用各式框架與限制去摸索、重建世界,每人似乎掌握了真相的一部分碎片,透過拼湊、透過聆聽、透過理解,我們能夠逐漸回憶起已倒塌的聳高塔影,也開始能夠想像彼此都能真正溝通的和諧願景。
翻譯,更樸實一點說,也許就是窺視人類境況的寓言,在分歧之後,在理解之前,在我們確然知道對方要表達什麼的瞬間,那種開心的感覺。
書籍資訊
書名:《你的耳朵裡是魚嗎?為什麼翻譯能溝通不同文化,卻也造成誤解?從口譯筆譯到自動翻譯,「翻譯」在人類的歷史如何發揮關鍵影響力》 Is That a Fish in Your Ear? Transl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作者: 大衛‧貝洛斯(David Bellos)
出版:麥田
日期:2019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