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生於阿爾及利亞,是土生土長的法國移民第三代。這麼說或許並不完全正確,因為在卡繆出生時,阿爾及利亞並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而僅是法國在北非的一處殖民地。法國「內地」的白人並不是「移民」到阿爾及利亞,而是遷居到阿爾及利亞。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阿爾及利亞人」在歐洲指的是像卡繆這樣的法國裔白人。其餘不是白皮膚但佔大多數的阿爾及利亞居民,則被粗率地統稱為「穆斯林」。就事實描述來說也不算有錯,阿爾及利亞的人口中有一部分是柏柏人,說柏柏語,從公元前一萬年就住在這裡;另一部分則是八世紀之後定居於此的阿拉伯人,說各種阿拉伯語方言。柏柏人跟阿拉伯人加起來,佔了阿爾及利亞人口的99%,他們曾經不被當做是阿爾及利亞人,只是一群「穆斯林」。
1962年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獨立,原本沒有名字、面目不清的「穆斯林」族群取回了「阿爾及利亞人」這個名字。至於像是卡繆這類白皮膚的人,則回到原本的稱呼:「法國人」。從外表看起來,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已經終結了半世紀以上,但是有另一種更為強大的殖民卻依然繼續,而這已經無關乎法國本身的意志──根據阿爾及利亞作家卡梅‧答悟得的說法,是阿爾及利亞人自己,在精神上拒絕讓法國的殖民結束,他們的時間毀壞,永遠停在獨立戰爭前夕。
卡繆的小說《異鄉人》中,主角毫無理由的殺了一個阿拉伯人。他並不認識這個阿拉伯人,不知道對方的名字,也沒有任何的深仇大恨。他的殺戮既沒有意義也沒有理由,主角因為自己對於世界的冷漠無感而被判處死刑。
七十年過後,卡梅‧答悟得寫了一本小說,宛如鏡像一般,從本該無名無姓被殺掉的那個阿拉伯人兄弟的視角,說了另一個故事,稱為《異鄉人:翻案調查》。這本小說不僅在阿爾及利亞暢銷,也引起了法國人的關注,卡梅‧答悟得因此獲得龔固爾首部小說獎。《異鄉人:翻案調查》如今已經翻譯成37種語言。

《異鄉人:翻案調查》是一本挑戰殖民主義觀點的著作,同類的小說我們第一時間可能會想到多明尼加白人移民後裔珍‧瑞絲的《夢迴藻海》(Wide Sargasso Sea),這部小說把焦點放在《簡愛》故事中來自牙買加的羅徹斯特太太柏莎,拒絕讓她淪為推進劇情進展的「瘋狂家具」,豐富而詩意的描繪了羅徹斯特先生如何壓制這位原本充滿靈感與夢想的女性,連原本的名字安托阿內特都奪走,改為更為英國化的柏莎,最終逼得她精神失常。
《簡愛》已經被認為是女性書寫的文學經典,但《夢迴藻海》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視角,補足了原作中的歧視本質,亦即把不討人喜歡、阻礙男女主角戀情的角色設定成出生在海外殖民地的混血瘋婦。
對英國人夏綠蒂‧勃朗特來說,把喜怒無常宛如動物的瘋女人設定為中南美洲的混種白人似乎是相當合理的選擇。這樣的存在必然具備著一些歐洲白人的特質──譬如美麗的外表──才能吸引到男主角,但也具備著不屬於白人的、更接近動物的特質──譬如精神疾病──來讓男主角合情合理的遠離她。
卡繆的《異鄉人》設定在阿爾及利亞,阿拉伯人在海灘上遭到無情地殺死。但全世界的讀者,除了阿爾及利亞人以外,恐怕未經提示都不會特別注意到地點到底在哪裡。卡繆的「歐洲性」被放在聚光燈底下,而他可能自認為很堅持的「阿爾及利亞認同」則被淡淡地擱在一邊。就像那個被殺掉的阿拉伯人一樣,不需要有名字,不需要有背景。
在小說推廣初期,卡梅‧答悟得與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編輯會開著車子,載著一箱書到各個城鎮開讀書會,參與民眾當然就是阿爾及利亞的地方父老鄉親。答悟得說,不管走到哪個地方,讀者都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很討厭卡繆,一種不認識卡繆,一種則是很喜歡卡繆。奇怪的是,不管走到哪個城鎮,一定都會有阿爾及利亞的讀者舉手,帶點氣憤地問同一個的問題:
「可是卡繆說,正義跟媽媽之間,他會選他媽媽耶!?」
卡繆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之時,正是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刻。卡繆並不支持阿爾及利亞解放陣線,在《世界報》的訪談中,他解釋自己為何不願意支持獨立運動,原句是這樣的:「人們開始在火車軌道上面放炸彈,我媽可能會在其中一輛火車上。我相信正義,但在正義面前,我會先為媽媽辯護。」
卡繆的處境是為難的,他某方面來說確實關心自己的出生地阿爾及利亞,但在正義(終結殖民、民族自決)與媽媽(作為法國殖民者後代的血統與文化傳承)之間,他終究選了媽媽。許多阿爾及利亞人無法原諒卡繆竟然選了媽媽。然而答悟得指出:「選媽媽不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嗎?為什麼他是卡繆就不可以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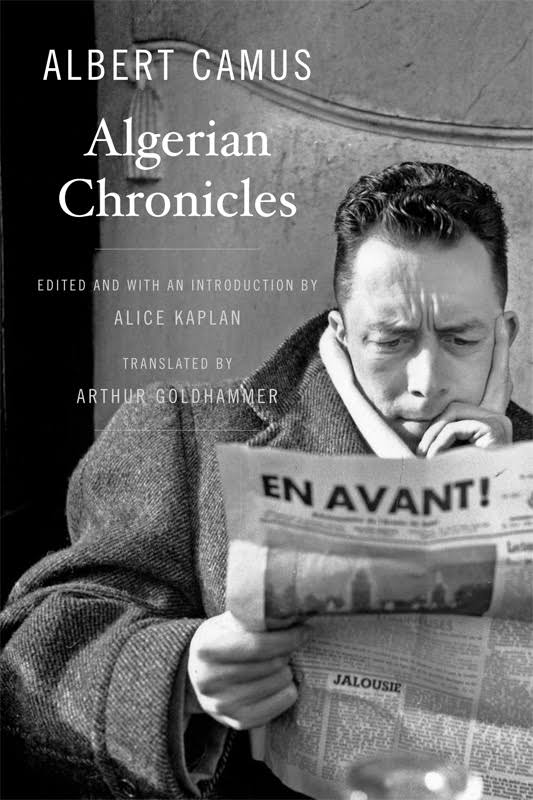
答悟得在寫出《異鄉人:翻案調查》之前,就已經是阿爾及利亞當紅的新聞評論員,擁有相當高人氣的專欄,並且毫不避諱批評時政。因此許多人以為他的小說也會戰力高張,或許會好好的數落卡繆一頓,結果買了發現完全不是想像中那樣,而就是一本文學小說,因此感到非常失望。對答悟得來說,他覺得計較卡繆當初的政治偏好沒有太大的意義,真正的問題恐怕反而是,卡繆是阿爾及利亞人心中徘徊不去的法國幽靈的一部分。物質的法國已經不再掌握阿爾及利亞,但想像的法國卻一直籠罩不去。
從1962年獨立之後,阿爾及利亞一直是由同樣一個政權所統治。這個政權由一群「功在阿爾及利亞」的政治人物、學者、軍人所組成,他們取代了原本的殖民者,卻變成了新的專制獨裁者。答悟得引述他的朋友的話語:「阿爾及利亞是隱形的,就像是北非的北韓。」阿爾及利亞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盡可能保持與外界不接觸,盡可能的延續同一批執政者的政治生命,儘管他們都已經80多歲了。
原本的阿爾及利亞總統包特夫里卡也是當初打過獨立戰爭的「殖民解放英雄」,他已經壓倒性的連任四屆總統,2019年他又要出來選第五次。包特夫里卡已經太過年老虛弱,甚至沒有辦法親自出來競選,於是他的人馬就拿一張照片出來選舉。這讓期待改革的阿爾及利亞青年感到很失望,於是引發了抗爭,最終遭到鎮壓而結束。包特夫里卡不選了,然而改革沒有發生,只是換成另外一批打過獨立戰爭的八十幾歲老人繼續掌權。
對答悟得來說,阿爾及利亞是一個拒絕讓殖民真正結束的國家,法國不在國境裡,在每個人的腦袋裡,當需要專政跟自肥的時候,同一批垂垂老矣的人物就跑出來叫喊:「法國人很壞,要不是我們救了大家…」這是一群拒絕死亡,拒絕繁衍,拒絕新生的過氣英雄,而他們的台詞「你們不要想太多,我們會保護你」跟故事裡的大反派法國,也沒有什麼分別。
「在敵人身上,我們總能看到變形的自己。我們之所以恨他們,是因為我們能從他們身上看見與自己相似的部分。」這是答悟得詮釋《異鄉人》與《異鄉人:翻案調查》為何如此相像的理由。那個沒有名字的阿拉伯人,與那個不知道怎麼搞的竟然殺了我兄弟的法國人,是同一組音樂盒裡不同的零件。
那些冒死爭取阿爾及利亞自由的人,跟那些死都不放阿爾及利亞自由的人,也是同一組音樂盒裡不同的零件。在正義跟媽媽之間,有些人不選擇正義,也不選擇媽媽,他們選了自己。
(本文部分資料來自於卡梅‧答悟得訪台於2019年11月8號在哲學星期五演講內容)
書籍資訊
書名:《異鄉人:翻案調查》 Meursault, contre-enquête
作者: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
出版:無境文化
日期:2019
圖片credit:Bertrand Langlois/AFP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