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
譯|葉品岑
在今日的預設立場中,人類幾乎無所不能。我們可以,起碼自認為可以,從細胞和化學的角度理解疾病生成的原因,因此應該能夠透過遵循醫學立下的規矩避免生病:拒菸、運動、接受例行性醫療篩檢,以及只吃時下觀念認為健康的食物。任何沒照著做的人,形同自己找死。或者換個說法,如今每個人的死亡,都能被理解為自殺。
開明的評論者不贊同這個觀點,認為那是某種形式的「責怪受害者」。在《疾病的隱喻》裡,蘇珊.桑塔格反對對疾病做暴虐的說教,指出疾病越來越被描繪成一種個人的問題。她說,人們學到要「注意口腹之欲。妥善照顧自己。不能放自己自由」。她指出,就連沒有明顯生活方式關聯的乳癌,也能被歸罪於一種「癌症性格」,有時被定義為心裡藏著壓抑的憤怒,這樣的人大概可尋求心理治療的幫助。即便主要的乳癌倡議團體也沒對可能的環境致癌物,或激素代替療法等致癌醫療體系多做評論。一九九八年的英國官方健康「綠皮書」總結,「就看個人要不要選擇改變自己的行為,過更健康的生活。」
當富人竭誠服從最新的健康生活規定──在日常生活中增添全穀物和健身時間──不那麼富裕的人,多數時候被困在舒服、不健康的舊生活泥淖中,繼續抽著菸,享受他們的平價美食。窮人和勞工階級抗拒健康風潮有一些很明顯的理由:健身房會員資格並不便宜;「健康食品」通常比「垃圾食物」花錢。隨著階級分道揚鑣,認為下層階級刻意過得不健康的新刻板印象,迅速和他們都是大字不識幾個的粗人的舊刻板印象混在一起。我在為提高最低工資做倡議時就親身見識過。富裕的聽眾可能同情藍領工人微薄的低薪,但他們往往想要知道「為什麼這些人不好好照顧自己」,譬如為什麼他們要抽菸和吃速食?對窮人的關心通常帶有一絲批評。
還有蔑視。英國名廚傑米.奧立佛在二○○○年代自告奮勇,決定改變大眾的飲食習慣,首先從學校營養午餐做起。他用通常會出現在稍高檔餐廳的菜單品項(譬如新鮮葉菜和烤雞),取代披薩與漢堡。但這個實驗失敗得一塌糊塗。在美國和英國,學童們把健康的新營養午餐丟進垃圾桶,不然就是一腳踩扁它。母親們從學校柵欄遞漢堡給她們的孩子。行政人員抱怨新餐點大幅超出預算;營養學家指出餐點的卡路里嚴重不足。奧立佛反駁說,人們應該了解一般「垃圾食物」透過化學加工,提供鹽、糖和脂肪的成癮組合。不過,他下戰帖之前根本沒事先研究當地人的飲食習慣,而且似乎沒花心思考慮如何有創意地改良那些飲食習慣,大概也是落得如此下場的原因之一。在西維吉尼亞州,他當著眾人的面,說一名地方媽媽平常給她四個孩子吃的食物會「害死」他們,讓對方哭了出來,也讓父母們自此和他疏遠。
吃錯食物當然可能會有不幸的後果。但什麼是「錯的」食物?在一九八○和九○年代,有教養的各個階級全面抵制脂肪,提倡低脂飲食,記者蓋瑞.陶布斯論稱低脂飲食替「肥胖的流行」鋪路,因為人們為追求健康放棄了乳酪塊,卻改吃低脂甜點。指稱膳食脂肪和健康不佳有關聯的證據向來不太站得住腳,但階級偏見勝過證據:富含脂肪的油膩食物是窮苦無知粗人的食物;社會地位比較優越的人只吃乾巴巴的義大利脆餅和脫脂牛奶。其他營養素也隨著醫學見解的轉變,一下被追捧,一下又變得過時:事實證明高膳食膽固醇,像是牡蠣裡的膽固醇,其實不是個問題,而且醫生已不再推薦年過四十的女性吃鈣片。越來越多人視糖和精緻碳水化合物為主要健康殺手,譬如漢堡的麵包。若你吃漢堡薯條配大杯含糖飲料,大概過兩個小時,等到高糖效應退去之後就會餓了。餓了之後若吃更多漢堡薯條配大杯含糖飲料,你的血糖可能會永久性地升高,導致我們所謂的糖尿病。
速食被認為是無知者的食物,被貼上特別的譴責印記。電影工作者摩根.史柏路克刻意一個月三餐都吃麥當勞,並記錄自己體重增加二十四磅和膽固醇飆升的過程,拍出了著名的《麥胖報告》。我也曾因便宜易飽而吃過好幾個禮拜的速食,但這沒有對我造成可察覺的不良影響。不過,我必須特別指出,我是有選擇性地吃速食,不碰薯條和含糖飲料,但吃雙倍的蛋白質。後來某著名食物作家就速食的主題電訪我,我一開口就提到了我的最愛(溫蒂漢堡和大力水手炸雞),但他覺得所有速食店都沒差。他想要的是對速食這個飲食分類的評論。對我而言,這像是問我對餐廳有什麼看法。
白人死亡潮
若食物選擇界定了階級的差異,抽菸則是把階級阻絕在外的防火牆。抽菸的人在幾乎每個工業國家都形同被社會遺棄之人,幾乎就像是鬼祟的告密者。我成長的一九四○和五○年代是另一個世界,那時香菸不僅能慰藉寂寞,還是一種強大的社會黏著劑。人們在酒吧、餐廳、工作場所和客廳互相請菸,為彼此點火,無論在室內或戶外,幾乎到了有人的地方就有菸味的程度,成了一種家的氣味。在約翰.史坦貝克一九三六年的小說《勝負未決》中,憤世嫉俗的年長工頭請年輕的移民工人抽剛捲好的菸,順便給他一些提點:
你要開始抽菸。抽菸是個不錯的社交習慣。你這輩子得和很多陌生人說話。請人抽菸,甚至向人要根菸,是我所知能最快讓陌生人卸下心防的方法。而且若有人請你菸但你拒絕,很多人會覺得被冒犯。你最好開始抽菸。
我的雙親抽菸;我有個祖父能單手捲菸;我的阿姨在我青春期的時候教我抽菸,後來她死於肺癌。政府似乎是贊成抽菸的。一直到一九七五年,軍隊才停止將香菸包含在糧食配給裡。
隨著比較富裕的人放棄這習慣,反菸戰爭(總被呈現的像全然善意的意圖) 開始變得像是一場對付勞工階級的戰爭。當雇主提供的休息室禁菸,工人只好到戶外忍受風吹雨打,他們總是靠著牆為香菸擋風。當勞工階級的酒吧紛紛變成無菸酒吧,他們的顧客只好三三兩兩私下喝酒抽菸,幾乎沒剩太多室內場地能讓他們聚會聊天。不斷上漲的香菸稅對窮人和勞工階級傷害最大。在街上買單枝香菸是他們的出路,但奇妙的是這些「散菸」在大部分地方都不合法。一名史坦頓島居民艾瑞克.賈爾納在二○一四年就因犯下此罪被市警鎖喉致死。
人們為什麼抽菸?最常見的解釋是同儕壓力讓人開始抽菸,這點史坦貝克的小說可以為證,而後尼古丁的成癮性則讓他們沒有太多選擇。抽菸本身的愉悅不太有人探索,彷彿光是提一提就會削弱反菸的初衷。二○一一年有篇專欄文章是個例外,一名記者帶種地主張:
我愛抽菸,我喜歡菸在飯後或配調酒的味道,我喜歡它能抵擋無聊,我喜歡在汗流浹背的熱天抽,也喜歡在冷冽的冬夜抽……說到底了,抽菸的儀式和習慣,更別說裡面還有尼古丁,令我感到平靜,令我放鬆。
尼古丁會活化大腦的「獎勵迴路」,以至於重新活化這個迴路成了一種自我撫慰,一種抵銷壓力和過勞的方式,偶爾還能化解無聊。我曾在休息室還准許抽菸的年代做過餐廳的工作,很多工人放任菸灰缸上的菸就這麼燃著,好讓他們能在忙裡偷閒時免去重新點菸的麻煩,立刻吸上一口。他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老闆或顧客;抽菸是他們為自己做的唯一一件事。在少數探討人為什麼抽菸的一份研究中,英國社會學家發現,抽菸在勞工階級的女性之間與更大的養家責任有關──而這再度透露出某種挑釁式的自我撫慰。
「壓力」這個概念在二十世紀中葉被製造出來時,人們注重的是管理階層的健康,因為他們的焦慮大概勝過無須做重大決定的體力勞動者。然而,事實證明,人們感受到的壓力多寡(這可用血液中的壓力荷爾蒙皮質醇來測量)會隨社經地位下滑而增加,承受最大壓力的是對工作最沒掌控權的那群人。在餐飲業,壓力集中在必須即時回應顧客要求的人身上,而不是坐在企業辦公室討論未來新菜單的人。在工作場所的壓力之外,還有貧窮帶來的種種挑戰,兩者相加就成了高度抗拒反吸菸宣導的組合──就像琳達.提拉多報導自己身兼兩份工作還要養兩個小孩的低薪工人生活:
我抽菸。抽菸很花錢。抽菸也是最棒的選擇。是這樣的,我總是毫無例外地精疲力竭。菸給我刺激。當我累得無法再多走一步時,我可以抽根菸,然後再做上一小時工作。當我被激怒,或被打倒,或沒辦法再完成一件事時,我可以抽根菸,然後會覺得好一些,哪怕只是一分鐘。這是我唯一可享有的放鬆。
低薪工人的壓力絲毫沒被紓解。相反地,若過去標準的藍領工作是一週四十小時、年休兩個禮拜、享退休年金和健康保險,對藍領的新期待則是視雇主需求隨時待命、沒有補助津貼或任何保障。有些調查如今發現美國零售業工作者絕大多數沒有固定工時——雇主想要他們時,他們就得上班,而且無法預測自己每個禮拜能賺多少錢,甚至每天能賺多少都不確定。隨著「即時化」排班的興起,工作者根本不可能提前計畫未來:你有足夠的錢繳交房租嗎?誰照顧小孩?而雇員「彈性」造成的後果可能和隨機電擊籠中的實驗動物一樣有害身心。
人口學家在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注意到,美國貧窮白人的死亡率出乎意料地小幅上升。這情況理當不該發生。將近一個世紀以來,令人寬慰的美國敘事總是在說,更好的營養和醫護會保障所有人活得更久。這情況尤其不該發生在白人身上,相較於有色人種,他們占盡優勢,向來擁有較高收入、較好的健康保險資源、住在比較安全的社區,而且不像深色皮膚的人得每天遭受侮辱和傷害。但黑人和白人預期壽命的差異卻逐漸縮小。起先,部分研究者不覺得貧窮白人越來越高的死亡率有什麼好吃驚:窮人的健康習慣不是本來就比富人差嗎?他們不是愛抽菸?
根據《紐約時報》表示,第一批注意到死亡率差距的經濟學家亞崔安娜.雷勒斯慕尼提出的說法是「作為一個群體,教育水準較低(而且因此大抵比較貧窮)的人,越沒有能力為未來做計畫,以及會延遲享樂。倘若如此,那或可解釋教育水準較高和較低族群間的吸菸率差異」。幾年後,另一名研究者、智庫蘭德公司的經濟學家詹姆斯.史密斯擴充這個觀點:窮人似乎沒意識到「很多你可能會做的事沒有立即的負面影響──飲酒過度、抽菸和嗑藥(給人短暫的快樂)──但實際上,它將在日後害死你」。
換句話說,貧窮的美國白人正在自殺,而這可不是單純的數據回落。在二○一五年年末,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和經濟學同僚安妮.凱思的共同研究贏得諾貝爾獎,顯示富裕和貧窮白人男性之間的死亡率差距正逐年擴大,白人女性間的差距則比較小。幾個月後,「布魯金斯研究院的經濟學家發現,一九二○年出生的男人,收入前百分之十和後百分之十的預期壽命差了六年。這個差距在一九五○年出生的男人之間是十四年,增加了比一倍還多。」抽菸僅占額外死亡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餘顯然是死於酗酒、鴉片類物質成癮,和真正的輕生──而不是以不明智的生活選擇象徵性地自殺。
(本文為《老到可以死:對生命,你是要順其自然,還是控制到死?》部分書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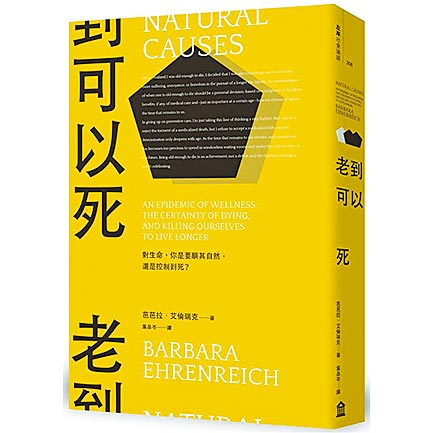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老到可以死:對生命,你是要順其自然,還是控制到死?》 Natural Causes: An Epidemic of Wellness, the Certainty of Dying, and Killing Ourselves to Live Longer
作者: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
出版:左岸文化
日期:2020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