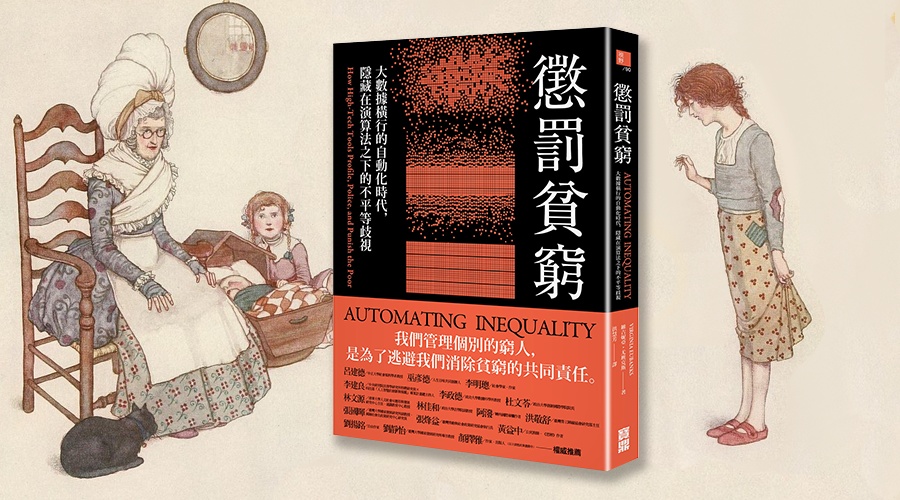
文|Virginia Eubanks
譯|洪慧芳
二○一七年四月,一個溫暖的春日,我徒步到公立圖書館,去找洛杉磯郡立濟貧院的照片〔如今稱為「朋友牧場」(Rancho Los Amigos)〕。途中,行經第五街與南大街的交叉口時,我看到一位黑人大叔,他戴著粉紅色的球帽,穿著髒汙的連帽衫,站在人行道上,伸出雙手揮舞著,痛苦地轉動著身子,彷彿遭到強風吹拂似的。他正在慟哭,一種高亢但出奇輕柔的聲音,介於歌唱與抽泣之間,沒有任何言語。數十人從他的身邊若無其事地經過,有白人、黑人、拉美裔、遊客、在地人、富人和窮人。每個人經過他搖擺的身子時,都看往別處,嘴角緊閉,沒人停下來問他是否需要幫忙。
在美國,貧富比肩並存,這種對比在洛杉磯的市中心特別鮮明。那裡的都市專業人士每天喝著拿鐵,滑著智慧型手機,窮人也在近在咫尺的地方生活。不過,在美國的每個都市與鄉鎮裡,生活困苦的人與生活無虞的人之間都有一道無形的隔膜。我在印第安納州的蒙夕、賓州的芒霍爾都看到了這道隔膜,在我的家鄉也看到了。
美國的窮人並非隱於無形,我們都看得見他們,只是把目光移開了。
這種視而不見的鴕鳥心態是根深柢固的,這也是解釋美國一個基本事實的唯一方法:在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中,多數人都會經歷貧窮。馬克.蘭克(Mark Rank)做過一份開創性的生命歷程研究,他的研究顯示,百分之五十一的美國人在二十歲到六十五歲之間,至少有一年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他們之中有三分之二會尋求社福救助,例如貧困家庭臨時援助(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TANF)、一般救助(General Assistance)、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住房補助、補充營養援助(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SNAP)或聯邦醫療補助。然而,我們仍假裝貧窮是一種令人費解的反常現象,只發生在極少數的病態人士身上。
在美國,我們與貧窮的關係一直帶有一種特質:社會學家史丹利.科恩(Stanley Cohen)稱之為「文化否認」(cultural denial)。文化否認使我們知道殘忍、歧視、壓迫等現象,但從不公開承認它們的存在。這是我們瞭解哪些事情不要去觸碰的方法。文化否認不單只是一種個人的個性或心理屬性,也是一個由學校、政府、宗教、媒體、其他制度所塑造及支持的一種社會過程。
我們在洛杉磯公立圖書館附近經過那位痛苦的大叔時,沒問他是否需要幫忙,因為我們都覺得自己幫不上忙。我們與一個人擦身而過,卻避免目光交流,這表示我們心知肚明:不要交流比較保險。我們不願相視,是因為我們正在進行一種「視而不見」的文化儀式,有意無意地放棄我們對彼此的責任。我們感到內疚,是因為感受到痛苦卻無動於衷。這就是否認貧窮對我們這個國家所造成的影響。我們不僅避開街角那個人,也避開彼此。
否認令人疲憊,而且代價高昂。明明看見了,卻要裝成視而不見,那是一種認知衝突。長時間忍受這種認知衝突是很累人的。那扭曲了我們的地貌,當我們打造基礎設施時(例如郊區、高速公路、私立學校、監獄等),那導致中產階級積極地避免跟窮人與勞工階級生活在一起。那也削弱了我們身為政治共同體的社會紐帶。無法直視他人的人,會覺得集體治理很難。
在美國,我們是以定義貧窮的方式來積極否認貧窮的存在。我們在某個時刻任意決定一個收入數字,然後定義收入低於那個數字就算是貧窮。官方定義的貧窮線,讓貧窮看起來像一種令人遺憾的反常現象,可以用糟糕的決定、個人行為、文化病理等原因來解釋。但實際上,許多人是反覆經歷暫時性的貧窮狀態。他們的背景五花八門, 行為舉止也近乎無限多元。我們的公共政策習慣指責貧窮,而不是補救貧窮的負面影響或消除貧窮的根源。這種對「個人責任」的痴迷,使我們的社會安全網只願救助那些道德上無可指摘的人。誠如二○一七年政治理論家雅莎.蒙克(YaschaMounk)在著作《責任時代》(TheAge Of Responsibility)中所說的,我們龐大又昂貴的公共服務官僚體系的主要職能, 是調查個人的苦難是不是他們的自身過錯造成的。
媒體與政治評論員都否認貧窮。他們把窮人描繪成病態地依賴社會的少數群體,而且對中產階級的社會構成了威脅。無論是保守派還是自由派都這樣想:右派往往譴責窮人是寄生蟲,左派則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對於窮人無法自立自強感到絕望。把窮人與貧困社區塑造成毫無希望或毫無價值的樣子,是一種極其偏狹、片面的想法。那導致多數人輕描淡寫或否認貧窮,連那些親身經歷過貧窮的人也是如此。
我們習慣否認貧窮,只有在窮人與勞工階級進行破壞性抗爭、發起草根運動以直接挑戰現狀時,才會承認貧窮的存在。誠如弗朗西絲.福克斯.派文(FrancesFox Piven)與理查.克拉渥德(Richard Cloward)在經典著作《窮人運動》(PoorPeoples Movements)與《規範窮人》(Regulating the Poor)中所說的,當窮人為權利及生存而群起抗爭時,他們才會獲勝。但管理貧窮的機制——濟貧院、科學慈善運動、公共福利制度等等——有驚人的調適力與持久性。儘管管理貧窮的機制隨著時間經過不斷地改變型態,但它們對窮人的分隔、限制、監管和懲罰始終都在,從未消失。
例如,一八七七年鐵路大罷工不僅突顯出窮人的苦難,也突顯出他們強大的政治力量。窮人與勞工階級的激進行動嚇壞了菁英階層,迫使菁英階層做出大幅的讓步:回歸以發放現金與物資為主的濟貧方式,不再強制收容。但不久,科學慈善運動就取而代之,只是方式改變了——科學化的社福個案調查專注在調查與監管,而不是把窮人關在類似監獄的地方,但結果是一樣的。成千上萬人得不到公共資源,家庭遭到拆散,窮人生活受到審查與管制,陷入險境。
這個模式在經濟大蕭條時期重現,在一九七○年代反對福利權運動時又再次出現。現在,這種事情又發生了。
簡言之,當美國的窮人與勞工階級變成一股政治力量時,救濟機構及它們的管制技術就會變得更利於文化否認,並把強迫窮人順從的方式加以合理化。救濟機構不僅破壞了窮人與勞工階級的集體力量,也讓其他人變得漠不關心。
*****
當我們談論那些在民眾與公共機構之間運作的技術時,我們比較關注它們的創新,以及它們突破傳統的方式。支持者稱這種技術為「顛覆力」,說它們顛覆了老舊的權力關係,創造出更透明、更迅速回應、更有效率,甚至本質上更民主的政府。
這種對新事物的過分關注,使我們忽視了數位工具嵌入舊有權力與特權體系的方式。雖然印第安納州的自動化資格認證系統、洛杉磯的協調入住系統、阿勒格尼郡的風險預測模型都走在技術尖端,但它們也是根深柢固、令人不安的歷史的一部分。濟貧院這種美國制度,比憲法還早出現一百二十五年。如果你以為一個統計模型或排名演算法就能神奇地顛覆幾個世紀以來建立的文化、政策、制度,那只是幻想罷了。
就像以磚瓦蓋成的實體濟貧院,數位濟貧院也在隔離窮人,讓他們得不到公共資源。就像科學慈善運動,數位濟貧院也會調查窮人、加以分類,把窮人當罪犯看待。就像反對福利權期間所出現的工具,數位濟貧院使用整合的資料庫來鎖定、追蹤、懲罰窮人。
在前面幾個章節中,我以實地考察的方式,讓大家看到新的高科技工具如何在全美各地的社服專案中運作。聆聽這些工具所鎖定的對象非常重要。他們講述的故事,和行政人員與分析家所講的不同。現在,我想把視角拉遠,讓大家以鳥瞰的方式瞭解這些工具如何一起運作,創造出一種管制窮人的隱蔽系統。
阻止窮人使用公共資源:印第安納州
數位濟貧院阻止窮人與勞工階級取得公共資源。印第安納州把福利資格自動化與民營化結合起來,因此大幅減少了福利救濟人數。僵化的行政程式與不合理的預期,阻止民眾取得他們理當享有的福利。糟糕的規則與設計不良的績效指標,導致程序一旦出錯就歸咎到申請人身上,而不是州政府或承包商。他們假設自動化決策工具永遠不會出錯,所以電腦化決策凌駕了為申請人提供程序公正的程序,導致數百萬人的福利申請遭拒。
然而,這種刻意的阻撓只達到有限的成效。在印第安納州,福利被剝奪而造成的明顯苦難引爆了人民怒火,掀起激烈的反彈。那些被剝奪福利的民眾開始公開他們的遭遇,維權人士開始號召盟友,提起訴訟。最後,印第安納人贏了⋯⋯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贏了。州長丹尼斯撤銷了IBM的合約,家庭與社會服務局推出混合式登記系統,該州參與貧困家庭臨時補助計畫的人數依然處於歷史低點。
印第安納州的資格自動化實驗之所以失敗了,是因為它沒有針對「不配」獲得福利,創造一個令人信服的故事。州長對窮人的敵意是不分青紅皂白的。自動化系統波及六歲女孩、修女、因心臟衰竭而住院的祖母。維權人士認為這些人是無辜的受害者,那項計畫違背了印第安納人博愛與慈悲為懷的天性。
雖然自動化社會隔離系統在全美各地愈來愈多,這種階層壓迫策略有明顯的瑕疵。所以,當直接阻撓失敗後,數位濟貧院創造出某種陰險狡猾的東西:一種崇高的道德敘事,把多數的窮人當罪犯看待,同時為少數幸運者提供救命資源。
分類窮人,把窮人當成罪犯:洛杉磯
洛杉磯郡的無家可歸者服務提供者想更有效率地利用資源,更有效地與各方合作,或許他們也希望把一項令人揪心的任務外包出去:從六萬名無家可歸者中,挑選誰該獲得住房協助。
該郡協調入住系統的設計者表示,那個系統的目的,是配對最需要幫助的人與最適合的資源。不過,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協調入住系統的排名功能:那是一種成本效益分析。為長期無家可歸的最弱勢群體提供永久性的輔助住房,比把他們留在急診室、精神病院、監獄的成本低。為那些弱勢度較低的無家可歸者提供小額、有限期的補助金,以便快速重新安置,比讓他們變成長期無家可歸的成本低。對那些弱勢排名最高與最低的人來說,這種社會分類機制的效果很好。但是,像蓋瑞那樣的人,他們的生存成本超過可能幫納稅人節約的社福成本,所以他們的生活變得無人聞問。
截至本文撰寫之際,洛杉磯的無家可歸者中,共有二萬一千五百人沒有獲得任何援助,他們的資料在無家可歸者資訊管理系統中存放了七年。幾乎沒有什麼措施保護那些私密個資,洛杉磯警局不需搜查令就可以取得裡面的資訊,這是執法部門玩弄數據的伎倆。把治安管理系統與無家可歸者服務系統整合起來,模糊了維持經濟保障與調查犯罪之間的界限,也模糊了貧困與犯罪之間的界限,收緊了追蹤定位及誘捕那些無住所者的網羅。這張網先用資料系統撈進資料,再用道德分類系統來篩檢。
協調入住系統所收集的資料,也為洛杉磯的無家可歸者問題創造了一種新故事。這個故事有兩種發展方式。樂觀版的故事是說,更細膩的資料可以幫該郡及整個國家面對政府無法照顧無家可歸者這個大問題。悲觀版的故事是說,按弱勢程度來分類無家可歸者,這樣做本身就削弱了大眾對無家可歸者群體的支持。這讓中產階級覺得,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得到了幫助,那些無法獲得資源的人基本上是無法管理的,或根本是罪犯。
如果數位濟貧院只是像印第安納州那樣直接阻止窮人獲得公共福利,那還容易應對。但是,把窮人分類並把他們當成罪犯看待,是把窮人與勞工階級納入系統,並用那個系統來限制他們的權利,剝奪他們的基本需求。數位濟貧院不僅排擠窮人而已,它直接把數百萬人收編到一個控制系統中,不把他們當人看,也沒收他們的自決權。
預測窮人的未來行為:阿勒格尼郡演算法
評估洛杉磯成千上萬名無家可歸者以產生一套道德分類系統,做起來既費工又昂貴。以演算法預測,則是利用統計數據與現有資料來產生價值與資格分級,而不是以臨床診斷的方式來評斷個人。當阻止窮人取得資源的做法失敗,分類成本又太高時,數位濟貧院改用統計方法來推斷。像洛杉磯VI-SPDAT那種調查,是詢問一個人做過的行動;像阿勒格尼郡AFST那種預測系統,則是根據過去類似群組的行為模式,來推測某人未來可能採取的行動。
分類是衡量個體之於群體的行為,預測則是鎖定關係網絡。阿勒格尼郡的AFST是針對一個家庭中的每個成員執行,而不是只針對被檢舉的父母或子女。在新的預測方法下,你不僅受到自己行為的影響,也受到情人、室友、親戚和鄰居行為的影響。
與分類不同的是,預測是跨世代的。安琪與派翠克的行為會影響哈麗葉未來的AFST評分。他們使用公共資源也會提高哈麗葉的評分。塔巴莎童年就醫時,派翠克與CYF的爭執,也會導致哈麗葉成年後的評分增加。安琪與派翠克今天的行動,可能會限制哈麗葉的未來及其孩子的未來。
所以,預測模型的影響是加倍放大的。由於預測依賴人際關係網絡,而且跨越好幾個世代,它的傷害可能像傳染病一樣傳播,從最初的接觸點蔓延到親朋好友,再蔓延到朋友的人際關係網,像病毒一樣傳播到整個社群。
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貧困管理系統把那麼多精力放在臆測其觀察目標可能出現的行為上。那是因為我們整體上不太關心窮人的實際痛苦,比較關心他們可能對其他人構成的潛在威脅。
AFST是因應一個真正重要的問題。看護者有時確實會對孩子造成可怕的傷害,政府介入以保護那些無法自保的人是恰當的。然而,即使孩子可能受到很大的傷害,這也不是毫無限制地拿貧困家庭來做實驗的理由。中產階層永遠不可能忍受AFST評估他們養兒育女的行為。把這種制度套用在別無選擇的群體上是一種歧視,根本不是民主,實在不可原諒。
十九世紀,醫學院對大體解剖的需求日益成長,導致盜墓熱潮,嚴禁偷竊屍體的法律也應運而生。濟貧院的墓地迅速成為非法屍體交易的熱門地點。由於醫院與醫生對廉價屍體的需求日增,很多州紛紛立法,把窮人屍體的黑市交易合法化:濟貧院與監獄囚犯的屍體若無人認領,可以交給醫學院解剖。大體解剖對中產階級來說是無法想像的遺體對待方式,卻被當成窮人為科學做出貢獻的一種方法。法醫人類學家仍然常在濟貧院埋葬窮人的墓地裡,發現屍骨遭到變動的證據,例如腿骨與骨盆上的鋸痕,頂骨的頂部像蓋子一樣掀開。以前,我們在窮人的身體上做實驗;如今,我們拿他們的未來做實驗。
*****
新技術的發展往往伴隨著一種危險的奇想。那種想法莫名其妙地篤定,工具的革命必然會抹除過往的一切。我以數位濟貧院來打比方,是為了在談論科技與不平等時,抗拒這種抹除歷史與背景脈絡的做法。
郡立濟貧院與數位濟貧院的相似處相當明顯。它們都阻止窮人取得公共福利,限制他們的活動,強制他們工作,拆散他們的家庭,導致他們喪失政治權,把窮人當成實驗對象,把窮人視為罪犯,建構可疑的道德分類,讓中產階級可以在道德上疏離窮人,重現充滿種族歧視與階級歧視的人類價值等級制度。
然而,公共服務中的高科技工具與實體濟貧院之間的類比,在某些方面是不夠的。就像郡立濟貧院適合工業革命時代,科學慈善運動適合進步時代(ProgressiveEra),數位濟貧院為我們這個年代的特殊情況做了調適。郡立救濟院回應了中產階級對產業失業率上升的擔憂:它把那些失業勞工藏在濟貧院裡,但又把他們留在附近,以便突然有勞力需求時可以立即供應。科學慈善運動則是回應了在地菁英對移民、黑人、貧窮白人的恐懼:創造出一個同時控制資源取得及社會包容的價值階級。
如今,數位濟貧院回應的是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所說的:中產階級的「害怕墮落」。艾倫瑞克寫道,白人中產階級面對底層勞工階級的崩解、上層財富階級的荒謬擴張,以及國家日益多元化的人口結構,亟欲維持自己的地位。他們大致上已經放棄正義、平等、公正的理想。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前,他們日益強大的「反自由主義」心態在公開場合還不強烈。那是一種「狗哨式」的殘忍:他們不會容忍消防水柱朝著黑人學童噴灑,但也不譴責邁克.布朗(MichaelBrown)、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娜塔莎.麥肯納(Natasha McKenna)、伊澤爾.福特(Ezell Ford)、桑卓拉.布蘭德(Sandra Bland)遭到警方暴力執法致死的慘劇。現在已經不可能強制要求窮人絕育,但懲罰貧窮家庭、讓他們挨餓、把他們視為罪犯的福利改革卻得到了默許。數位濟貧院在這個政治時刻誕生,也完美地配合了這個政治時刻。
過去的濟貧院和現今的數位濟貧院雖然關係密切,但兩者仍有顯著的差異。以前的郡立濟貧院把窮人集中起來,無意間促成了不同種族、性別、民族血統之間的階級團結。大家同桌共餐時,即使被迫吃粥,可能也會發現彼此的經歷有相似之處。監控與數位社會分類把我們切分成愈來愈小的微型群體,以便做各種隱私侵犯與控制,這導致大家愈來愈疏離。當我們住在無形的濟貧院時,大家變得愈來愈孤立,即使其他人和我們一樣受苦,我們也因為與周遭斷了連結,不得而知。
(本文為《懲罰貧窮:大數據橫行的自動化時代,隱藏在演算法之下的不平等歧視》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懲罰貧窮:大數據橫行的自動化時代,隱藏在演算法之下的不平等歧視》 Automating Inequality: How High-Tech Tools Profile, Police, and Punish the Poor
作者:Virginia Eubanks
出版:寶鼎
日期:2022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