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這種武器,很少用於純粹善意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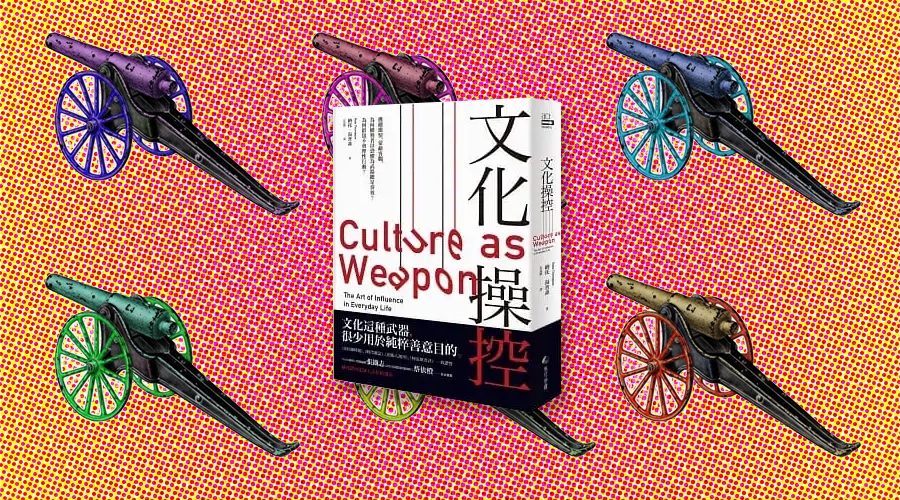
文|Nato Thompson
譯|石武耕
意識洗白
贈與,無論是透過大型的廣告專案、某家NGO在非洲提供的診療、還是把交換形式當成藝術所進行的贈與,已在二十一世紀成為人們高度關注的事。表現善行的形式,近年來也越趨豐富多樣。捐款救災、捐助無家可歸的人、在慈善晚會上捐獻、餽贈鄰人、捐款阻止氣候變遷、把贈與當成一種社會體驗的藝術創作。在原始社會,慈善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這種行動既是一種私人接觸,也是一門公共事業與生意。慈善有可能是個人的,也可能是集體的,可能很誠摯也可能有操弄性。一般來說,贈與往往有點兼具上述特質。
研究贈與的早期民族學家牟斯(Marcel Mauss),在他影響深遠的著作《禮物:交換的形式與功能》(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當中,就相當清楚地說明,交換與送禮在他所謂的「古式社會」(archaic societies)裡扮演複雜而基本的角色,並且由此帶出對於當代社會的交換所做的詮釋。牟斯認識到,既然一切的經濟都建立在交換上,那麼在他研究的這些社會中,贈與和收受禮物也與該團體複雜的權力安排、互惠、義務以及整體需求密切相關。當代資本主義雖然多多少少會讓人覺得,所有形式的交換都是等價的(這裡指的是不涉及團體的宗教、文化與社會義務,純粹以數字為準的等價關係),但牟斯卻指出,在歷史上不同的交換案例,贈禮行為都揭示集體需求的複雜性,從而擾亂了上述的當代觀念:
我們想在本書中單獨探討一種重要的現象,也就是理論上出於自願、無關利害且自動自發,但實際上卻出於義務且涉及利害的給付(prestations)。通常採取的形式是慷慨提供禮物,但是伴隨的行為則是形式上的刻意與社會欺瞞(social deception),這項交易本身的基礎就是經濟上的自我利益。
為了探討慈善的問題,牟斯從契努克語(Chinook)借用誇富宴(potlatch)這個詞彙。誇富宴並不只是出於仁慈的贈禮,而是一種以充裕的財富壓倒某個敵手或競爭者的習俗。誇富宴就是一份隆重到對方永遠還不起的贈禮,由此證明送禮方無可置疑的主宰地位。不囤積剩餘的財富,而是舉行誇富宴與做慈善,就是在以不同形式擴充權力。慈善仍然是種交換。就算不要求回報,這種交換也與權力和文化密不可分。牟斯所研究的,是古式社會裡的交換(亦可說是慈善)的複雜性,而當代版本的交換,受到全球經濟、廣告公司、NGO等因素的影響,又變得更複雜。
慈善是透過經濟與人際接觸表現出來的社會需求,無論是德蕾莎修女助人緩解苦楚,還是藝術家以慈善的方式騰出空間使公民意識覺醒,也許還有像金寶濃湯為了提升銷量而刊登慈善廣告。在從事慈善行為時,其中都有某種私密的人類情緒跟深層的社會需求,在推動由文化所驅使的消費社會。
從數據即可看出這一點,在二○一三年,全美國的慈善捐款金額已達三千三百五十一億七千萬美元,而且還在穩定攀升,其中大多都是私人捐款。這些數字應該不令人意外,從有人類文明以來,權力不均就一直是人們憂心的問題。耶穌對此也談了很多,而凱撒在臨死前也把他所有的財產、土地與錢財都捐給了羅馬人民。面對真相吧,普羅米修斯會死在岩壁上,也是因為他把火送給凡人濟助眾人(philanthropic)。
隨著人們開始思考贈與,也就會想到究竟何時是贈與,何時只是假裝贈與。記錄英格蘭富人生活的作者富勒(Thomas Fuller)就在他的著作《英格蘭顯貴史》(Worthies in England, 1662)裡討論慈善事業的善惡百態,他寫道,「日子過得就像狼,先把羊逼死,再把羊毛分給需要的人。」
既然有如此豐沛的金錢與能量,用在如此廣大的全球範圍助人,那就必須類比於治理(governing),來思考贈與行為的結構。要談論贈與,當然就必須更廣泛考量到恐將奪取(taking)體系正常化的結構。政府在本質上究竟是某種形式的贈與,還是某種形式的共享呢?
繼續追問下去,當然還有贈與金額何以如此龐大,以及將奪取正常化的體系如何得以延續的問題。或許不令人意外的是,在美國,捐贈金額激增與貧富不均惡化是同步的,因為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既提供了誘因鼓勵人們贈與非營利組織,也讓那些超級富豪大秀慈善事業。
二○一三年七月,身價數十億的投資人兼慈善家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之子彼得.巴菲特(Peter Buffet)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客座評論,批評他所謂的「慈善產業情結」。常常跟世界第一富豪吃飯並交換意見的彼得.巴菲特,用了一個獨特觀點來談論濟助行為(philanthropy)。
「為少數人創造龐大財富的體系毀掉多數人的生活與社群之時,『回饋』(give back)這個詞聽起來就越英勇。我會將此稱為『意識上的洗白』(conscience laundering),賺最多錢的人如果要覺得好過一些,可能就需要在慈善行動當中,讓大家雨露均霑。」
意識上的洗白,巴菲特聲稱,擁有財富的人確實需要洗滌自己的意識,這話聽著倒是順耳。言下之意是,慈善機構試圖解決的問題,正是世界金融化的競賽所造成的後果,因此也暗藏對於資本主義的批判。
用一隻手做壞事時,另一隻手做的在多少程度上算是好事,這或許就是慈善事業的效率。在這篇評論中,彼得.巴菲特還善用那些想幫助沒有特權者的心裡所掩飾的更廣泛的殖民主義欲望:
我太太跟我剛開始從事慈善事業時,就注意到慈善殖民主義的心態。贈與者會以某種方式「一舉成功」。對於特定地點所知甚少的人(包括我)會以為,他們可以解決當地的某個問題。無論這問題涉及務農方法、教育實務、職業訓練還是商機發展,我都一再聽到人們在討論,要把在某地奏效的辦法直接移植到另一地,可以不用顧及文化、地理或社會規範。
出於殖民心態的濟助行為傳統悠久。如果你年紀夠長,不妨回想一下巴布.吉道夫(Bob Geldof)與米茲.尤瑞(Midge Ure)在一九八四年那首紅遍全球卻不明事理的歌曲〈他們知道聖誕節到了嗎〉(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這是每到聖誕季電台都會播放的歌曲。為了替衣索匹亞的饑荒募集物資(其中毫無疑問也包括了羹湯)而寫的這首歌,找來當時幾位最紅的流行歌手參加演唱,包括了杜蘭杜蘭樂團(Duran Duran)、U2樂團的波諾(Bono)與亞當.克雷頓(Adam Clayton)、史汀(Sting)、喬治男孩(Boy George)、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菲爾.柯林斯(Phil Colins)、喬治.麥可(George Michael)、庫爾夥伴合唱團(Kool and the Gang)等等,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為止都是英國最暢銷的單曲。其中一些歌詞,就算不是直白的殖民主義,也愚蠢得難以置信(不明事理與殖民主義有時難脫關係)。以陷入戰禍與貧窮的非洲國家為題的這首歌,在結尾重複著這樣的副歌歌詞:「他們究竟知不知道聖誕節到了呢?」
如此天真的提問,與其說是讓人看懂歌曲的意涵,還不如說是讓人看透了這些歌手。在合唱部分把歌詞改成「我們知道自己在唱什麼嗎?」說不定還更點題呢。
這支八○年代的搖滾樂明星隊,驕傲而大聲地唱出了自己的一片好意。他們究竟知不知道現在是聖誕節呢?就算烈日當空、水源枯竭,不知道聖誕節到了還是最慘吧?這樣說你就懂了。有些人會說,這些搖滾巨星雖然明白這些歌詞帶有殖民心態,但也知道這類帶有種族歧視陳腔濫調的音樂能夠賺很多錢,好讓非洲的黑人兒童有飯吃。也許在做慈善時,只要能賺錢,就能容許一切罪過了吧。
再繼續恐怕會顯得太憤世嫉俗,援助產業當然也是做了善事,二○○四年的蘇門答臘海嘯、二○一○年的海地地震,或是二○一一年的日本海嘯等災變的救災資源當中,還是湧入來自許多國家與個人的援助。雖然這些資源的分配方式及實際效益都引發激烈爭議,但無可否認,也是因為在接連發生重大地質災變時,有這些金流湧入災區,才使得救援到達。
沒有緊急事態時,當然也有人進行慈善工作。非營利與遍布全球的NGO,也同樣經歷一番興盛的榮景。這些分別處理飢餓、學校或博物館等事務,必須以回饋社群為使命的機構團體,成為了提供照護、服務與文教的龐大基礎體系。據智庫「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指出,在二○一三年,全美國就有大約一百四十一萬個登記在案的非營利組織,為經濟貢獻將近九千零五十九億美元。
關於組織倫理以及援助目標有許多探討。在負面觀點方面,有人會說除了緩解苦難之外,慈善組織本身在整套基礎體制裡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也造成了這些需要救濟的問題。有人的論點則與談論社會福利時相似,他們認為慈善事業反而強化依賴,或者也有人會反過來主張,對於民間的慈善事業有迫切的需求,表示管治體系出問題。也有人會主張,慈善之於贈與者的意義終究多於接受者的意義,而援助的終極目標,也就是鼓勵自力更生。
但你當然也可以說,對於貧富差距擴大、資源越趨集中而急需幫助的人來說,援助產業仍是少數提供支援的單位之一。與其把社會弊病歸咎於慈善事業,倒不如將其視為減輕苦難的組織與作為,許多人在捐獻時就是這樣想的。
本章的篇幅有限,無法詳列關於慈善事業大幅成長與協作系統的複雜探討。實際上,這個產業的範圍太廣,使人難以辨別慈善事業與基本社會服務之間的界線。但在指出慈善事業無所不在後,現在我們要談的,則是透過動人號召以進行品牌經營的做法。
(本文為《文化操控:挑撥激情、蒙蔽客觀,為何權勢者創造恐懼總是奏效?為何群眾不會理性行動》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文化操控:挑撥激情、蒙蔽客觀,為何權勢者創造恐懼總是奏效?為何群眾不會理性行動》 Culture as Weapon: The Art of Influence in Everyday Life
作者:Nato Thompson
出版:馬可孛羅
日期:2022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