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1940年至1945年間,德國為彌補戰爭喪生的人口,在被佔領區進行大規模的外國兒童「日耳曼化」計畫。此項計畫由黨衛軍指揮官海因里希‧希姆萊下令執行,在波蘭、烏克蘭以及波羅的海國家有超過二十萬名兒童被偷,其中學齡兒童被送往特殊中心接受「亞利安」教育,讓他們相信自己是亞利安人,而較年幼的兒童,包括數量龐大的嬰兒,則先送往「生命之源」(Lebensborn),再交由德國家庭扶養。戰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RRA)與其他流亡人士救援機構共協助四萬名兒童找到出生家庭。
──《斷線》作者後記
有關於種族屠殺的惡行中,更甚於肉體消亡的便是文化滅絕:禁絕母語,與原生文化隔絕,進行洗腦教育⋯⋯當一個人和與之連結的文化被強制斷絕後,他就再也沒有歸屬,在靈魂深處淪爲風中飄零的落葉:失去原本的顏色,皺縮乾枯,凋零死去。
《斷線》書中橫跨祖孫四代的血緣雖然沒有間斷,但曾祖母艾禾起卻是家族斷根的起點,就像條斷掉的線。故事從最小的孫子「索爾」的視角開始,看著這一家四代間混亂的互動,觀念的衝突,文化認同的取捨。世代間或跨世代在不同議題、想法或是拉幫結派,或是結夥攻擊,宛如小型的戰場,總會有人(在認同上)肢體不全,傷痕累累。
每個人都曾六歲過,那個已經可以理解簡單事理的年紀,然而尚未有能力去分辨或得以選擇的權利,被動地接受灌輸。故事中的四位六歲小孩分別被不同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影響,除了最小的一代索爾還沒長大之外,另外三個人長大成人後都經歷不同程度的衝擊或創傷,然後又留給孩子更困惑、更難以理解的遺憾。下一代質疑上一代的認同或選擇,成人之後奮力對抗那些被加諸的認同或選擇,再依自己的方式去塑造他們的孩子。所有的人都曾試圖重新連起斷掉的線,然而在每個人的執念之下反而令「線」斷裂成更零散細碎的線頭。

艾禾的身分是「演唱家」而非「歌唱家」,從她歌喉發出的是飽含情感的聲音,不見任何歌詞,那是一個具有深層意義的暗示。
「我覺得聲音本身就是一種語言。」
這種「語言」的型態是最為原始,沒有母音,沒有詞彙,更沒有句子該有的構造。它甚至不是「母語」,艾禾無從得知她真正的母語為何,她的真正母語早在一開始的「生命之源」時起便遭到剝奪。她得到一個經過偽造、編織的出身,那個她原本以為熟悉的母語竟然是迫害者的語言,她試著尋找自己的根源卻毫無所獲。成年後的艾禾放任自我,恣意行事,雖然她的聲音揚名世界,但就像脫離枝枒的落葉,飛揚風中而不知根源何在。
艾禾的女兒莎荻因為母親的失落過往,極度渴望能補足家族失落的過去,她替自己找了個猶太人的身分認同,執著於填補空洞。然而莎荻忽略了自己的問題在於童年缺乏父母陪伴,「祖父母」的教養又過於嚴苛,她並未真正發現自己的創傷何在,成年後的莎荻無形中讓自己的執著對兒子杭達造成難以磨滅的影響。
莎荻過分苛求完美的態度令杭達產生陰影,雖然他已遠離生命之源的傷害,但他童年在以色列渡過的時光所面臨的情形是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間的衝突與矛盾,與永遠達不到母親期望的挫敗感。納粹迫害已是過往,杭達面對的是應許之地千百年來的紛爭,對一個六歲小孩來說實在太過沉重。原本是兩小無猜的童年玩伴,卻被教導去仇恨,曾經的杭達熱切懇求,想學習阿拉伯文化,但他開始學會去恨之後,竟成為一個滿口「阿拉伯人去死」的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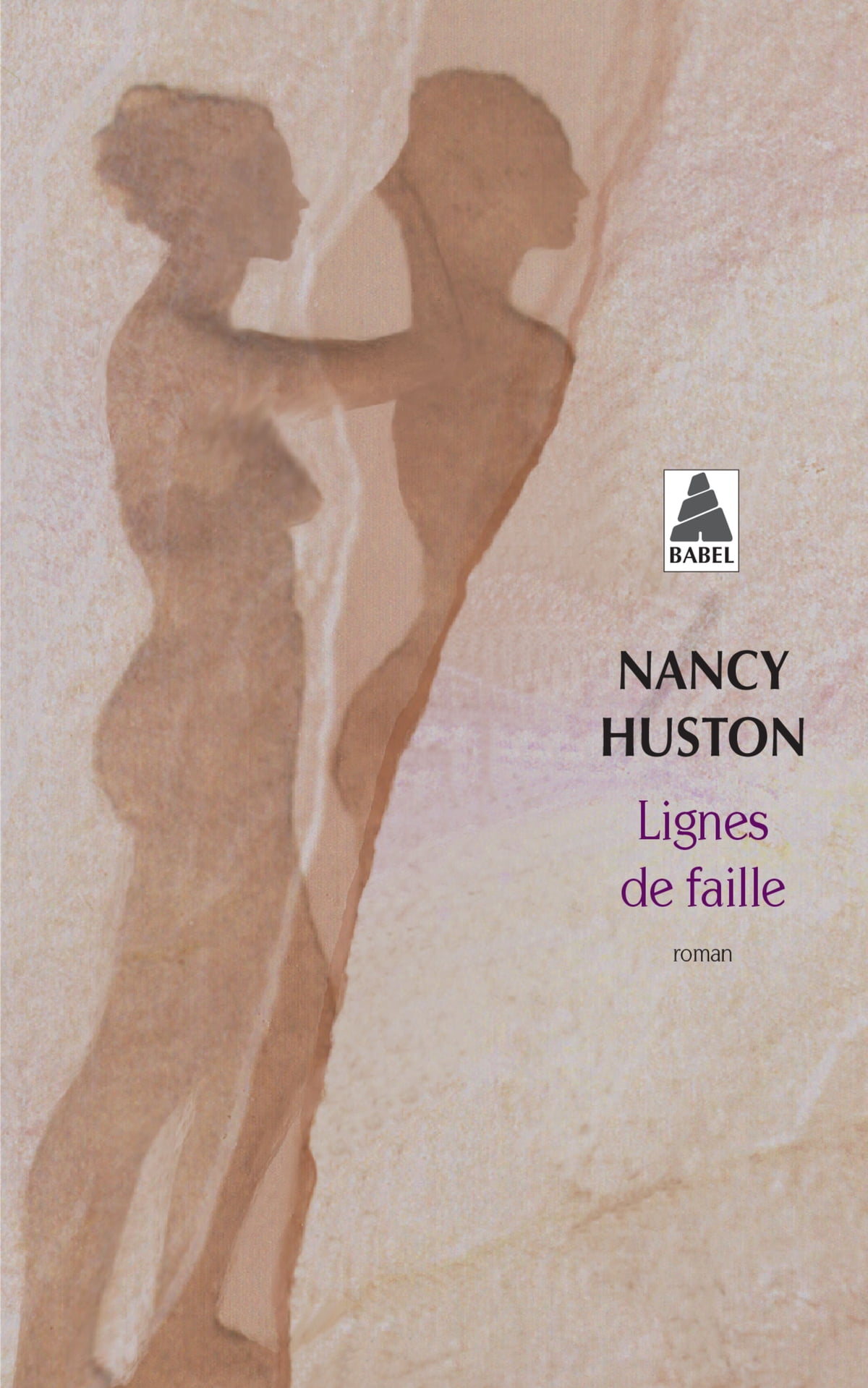
任性的艾禾、執著的莎荻、對阿拉伯人有著莫名仇恨的父親杭達,這些就是索爾看見的成人。美國小孩索爾,正逢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他懂得使用 Google 電腦科技,去搜尋戰爭的殘酷、血腥畫面,明明是直接衝擊,但因為隔著一片電腦螢幕,於索爾而言不過又是個獵奇的畫面罷了。他比那些長輩都清楚戰爭的面貌,情感上反而最為麻木。
如此聰敏的索爾當然能透徹看清自家長輩間的矛盾,也同樣不能感受到那種被刨根的失落。索爾被刻意教育成美國基督徒,斷了莎荻苦心想牽起的「線」。另外不止文化上的斷線,從艾禾以來所有人的身上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痣,代表肉體上,血緣上的連結,無論人生中遇到何種波折,艾禾、莎荻、杭達藉由撫摸他們的痣,心靈上總會得到些許慰藉。索爾的痣卻在父母的決定下被挖除,暗示著串連家族更深沉的那條線再一次地斷裂。這也呼應了索爾為何是生活最幸福的孩子,同時也是最麻木無情的人。
索爾和所有的大人都不明白,為什麼切除掉那個可能有害健康的痣後,傷口未隨時間好轉,只有更加惡化,他們沒人知道那是一種斷線的痛。當未來的某天,長大的索爾可能會因為某種不明的失落所苦,他可能不知道,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來自於好幾代以前的那場邪惡滅絕行動。
書籍資訊
書名:《斷線》 Lignes de faille
作者:Nancy Huston
出版:Actes Sud
日期:2006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