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常可以斷言說:朋友的婚禮就是友誼的葬禮。
―凱瑟琳.菲利浦寫給查爾斯.科特雷爾,一六六二年
文|Marilyn Yalom、Theresa Donovan Brown
譯|邱春煌
在女修院外,友誼的故事繼續由男人所寫,完全聚焦在男人身上。法國哲學家蒙田受到他對艾蒂安.博耶提柏拉圖式的愛啟發,寫下他頗具權威的論說文〈關於友誼〉,迅速加入亞里斯多德與西塞羅著作的行列,成為嚴肅探討友誼議題的三個基礎文本。其他十六世紀人文主義者如蒙田,繼續將理想的友誼概念化為品德高尚的男人透過個人、宗教、軍事和公民關係表現出對彼此的忠誠,這成為一種向上提升的經驗。
不過,在蒙田的一生中(一五三三~九二年),女人友誼的實際情況正變得愈來愈明顯可見。一五八○年代,英國一位人士觀察寫道,城市裡有錢人的妻子穿著精美服裝坐在門前,有時散步,有時騎馬,有時與其他女人玩牌,她們閒來「找找朋友陪伴談天,或是左鄰右舍串門子閒聊,甚至在分娩、洗禮儀式、上教堂和葬禮上也盡情歡樂;不過,這些舉止可都有獲得她們丈夫的首肯,因為這是習俗。」。
「閒聊」(gossip)一詞是女性朋友在十六世紀一個常見詞彙,並不像現在有流言蜚語或說長道短的貶損意涵。閒聊可以交換私人或社區有用的資訊,以不良行為為例,她們的談話會形成一種執行社會規範的方法。如果她們對某事的關心具有足夠的強度,鎮上的行政官員可能會倍感壓力,必須對違反者採取正式行動。「閒聊」一詞也被用在遺囑和法院紀錄等文件上,伊莉莎白時代閒聊者的形象也經常出現在舞台戲劇的表演當中。
莎士比亞世界中的女性友誼
莎士比亞(一五六四~一六一六年)觀察過社會各階層為數不少的女性友誼,從皇室到酒館都有:《溫莎的風流婦人》福特太太與佩吉太太、《冬天的故事》赫敏皇后及她的忠心友人寶琳娜、《仲夏夜之夢》赫米婭和海麗娜、《亨利四世:第二部》奎克莉夫人和達爾.提爾須特、《亨利五世》法國公主凱薩琳和婢女愛麗絲、《皆大歡喜》羅莎琳和表妹希莉雅、《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克莉奧佩特拉及女侍、《無事生非》總督的姪女畢翠絲和總督的女兒希羅、《威尼斯商人》鮑西亞和貼身女侍奈莉莎等等──這些女人都只是幾個莎士比亞創造出來,做為巷弄街坊和出身名門女士等閒聊的角色,她們相互協助擊敗男性的愚蠢、誤解及公然的暴力。
莎翁在這些作品中有絕大部分是在確認女性友誼的存在,同時也給予她們的友誼一些權利。為了處理情節,他經常藉由兩個女人相互配合的效果,產生圓滿的結局。以《溫莎的風流婦人》中福特太太與佩吉太太為例,這兩個女人遏阻了法斯塔夫想要誘惑她們的企圖。那個傲慢、嗜酒成性又迷人的無賴,對女人之間的關係所知不多,他寄給她們兩人各自一封情書。經過比對後,她們發現兩封情書的內容居然一模一樣,於是她們想出一個復仇妙計,要讓他難堪到無地自容。
在《威尼斯商人》中,鮑西亞喬裝成一位法學博士,她的貼身女侍奈莉莎則裝扮成她的助理,她們在法庭上為安東尼奧提出答辯。安東尼奧答應放高利貸的猶太人夏洛克,若無法還錢就割下自己的一磅肉抵債,於是這兩名女人相互支援,一搭一唱,使出詭計,讓安東尼奧脫身,讓他免受割肉之痛。
《冬天的故事》讓赫敏皇后及她的好友寶琳娜與國王雷昂提斯相鬥,雷昂提斯誣指他的孕妻通姦,把她送進牢裡。寶琳娜試圖將赫敏剛出生的女兒,帶到固執的國王面前來安撫他的心,不料他竟罵她是私生子,命令將她丟到宮廷外受風吹日曬雨淋。當然,由於這是一齣喜劇,劇終時母女兩人都獲救。最後,在赫敏忠心友人寶琳娜的努力不懈下,國王幡然大悟,一家三口終於團圓。
在《皆大歡喜》中,羅莎琳和希莉雅是表姊妹關係,也是閨中密友,她們兩人從小感情就非常要好:
我們睡在一起,
一起起床,一起念書,一起玩,一起吃飯,
我們的感情如膠似漆,不論我們去哪,
我們都一起去,難分難捨。
而,最後她們的親密關係逐漸淡化,各自發展男女之愛──在真實生活與在文學世界中一樣,男女之愛經常取代了女性友誼。我們可以看見,女人的友誼與婚姻起衝突,不僅在莎士比亞的舞台劇中上演,也在真實的生活中上演著,這個見色忘義的戲碼直到二十一世紀依然沒變。
傳記作家艾克洛德提醒我們,莎士比亞的母親有六個姊妹,她是么女,在家裡女人國中集三千寵愛於一身。莎士比亞可能從傾聽他母親與眾姊姊及女性朋友們的談話中,感受到女性團結的氛圍。在他的故居史特拉福,女人與男人一樣,和鄰居進行日常商業活動並相互幫忙,尤其是婆婆媽媽們被視為「社交行動派」,她們設立許多小組,作為一種非官方的警力在運作。
一份紀錄(意謂歷史上有許多類似的案例遺失)描述當鄰居的丈夫企圖謀殺他的妻子時,伊麗莎.妮爾由於介入其中,被她鄰居的丈夫殺死。這兩個女人是朋友嗎?根據伊麗莎墓碑上的墓誌銘,我們至少可以假設她們正在尋找彼此:「為了救她的鄰居,她流了血/和救世主一樣,她為了做善事而捐軀。」

尤其在婚前,伊利莎白女王時代的女人,絕大部分時間都與其他女人相處。五個女人之中約有一個終生未婚,這表示有相當多女人不結婚。進入二十世紀,與在莎士比亞時代一樣,單身女人睡同一個房間,甚至睡同一張床。在工人階級女人當中,當女孩離鄉背井來當學徒,擔任幫傭,或找其他工作時,沒有親屬關係的其他女孩經常取代姊妹床伴。
對十六世紀的十幾歲女孩來說,在郊區紳士階層家庭當女傭,或在十六世紀之後在倫敦大家庭做幫傭,乃司空見慣的事。她們在婚前平均花費約四年時間擔任傭人。社會不允許單身女人獨居,這可由一五六二年一項國會法案「技工法」獲得佐證。該法規定所有未婚女人必須就業,否則會被送入監牢。當然,這個極端法案並不是針對中、上層階級家庭的女孩。
勞工階級女孩彼此間同病相憐,需要互相扶持。我們不難想像,經過一天的辛苦工作,當蠟燭吹熄後,她們可能跟對方說些親密的悄悄話,安慰彼此,嘲笑其他人的怪癖,透露小祕密,相互取暖。白天時,兩個年輕女人一起做些家務,如清潔、煮飯、紡織、縫紉、洗衣、整床等等,或是當她們從市場、水井或教堂肩並肩走路回家時,或是在她們休假,在當地節日加入其他年齡相仿的女孩一同慶祝時,可能就有親近的機會。
當然,女人之間也難免會有爭吵發生,可以從涉及個人與家庭的法院爭議中得到佐證。尤其是成熟的女人被法院傳喚在審判中作證,在賣淫或巫術等「不當行為」案件中做出不利其他女人的證詞。女性證人經常對彼此家中的情況相當了解,通常只有要好的親朋好友才會知悉;她們沒有事先告知或不須俗套就跟左鄰右舍串門子,如果隔壁發生了什麼事,女人會先聽到風聲並可能私下探聽了解。有時比較卑劣的動機,像是嫉妒,會點燃女人對昔日閨密的妒火,相互指控對方性生活不檢點,甚至當眾演起全武行。這類事件偶爾會在好姊妹之間發生,甚至破壞婚姻,讓社區變得不安寧,這提醒我們:即使是生活中最要好的姊妹情誼也是很脆弱的。
除了爭風吃醋外,鄉下女人在河岸邊洗衣或是在市集販賣蔬菜,可能會在路邊停下來時跟其他女人聊聊最新的八卦消息,抱怨自己的丈夫或是哀悼孩子不幸早夭等等。許多女人依賴鄰居在緊急需要時伸出援手,如當她們分娩、生病或孩子需要保母照顧時。生產後坐月子期間― 生女孩四十天,生男孩三十天,給予新手媽媽臥床好好休息,適應哺乳,陪嬰兒玩,通常須有產婆、女性鄰居和嬰兒的外婆──如果有的話,在一旁陪伴著。坐月子是「女人的時間」,不須配合丈夫的需求,丈夫不但禁止與妻子同房,還必須挽起袖子幫忙做家事。坐月子即將結束時,新手媽媽會接受「淨化」儀式,也就是與她的嬰兒一起上教堂,嬰兒則由產婆抱在懷裡。教堂儀式完成後,新手媽媽的家裡會舉辦派對慶祝,她的朋友會提供蛋糕、啤酒等等食物。
遠親不如近鄰,因為女人通常嫁到遠離母親姊妹的他鄉,很少能回娘家,不論是步行、騎馬或搭乘二輪或四輪馬車,都需要長途跋涉。那些會寫字的女人──可能十個之中不超過一個,至少能透過書信與娘家的家人保持聯繫。但是,大多數不識字的女人主要還是依靠左鄰右舍的人情幫忙、相互慰藉,以及交換消息。

說話是女性展開友誼之所賴。說話的女人──可說是一個亙古永不過時的話題!所以我們將個人的第一語言稱為「母語」,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母親從嬰兒出生的那天開始,就對他說話、唱歌、唱兒歌,將從她母親和祖母那裡聽到的口述傳統傳承下去。在過去,男孩和女孩最初在嬰兒時期是從母親或女性照顧者學會說話。之後,某些男孩──如莎士比亞──被送到文法學校,少數女孩則上女子學校,她們在學校裡學習閱讀、縫紉,甚至寫字。在英國新教環境中,男孩和女孩都要能念聖經,但寫字只是非常少數人的一個選項。一六○○年時,只有約三分之一的男人和十分之一的女人可以寫出自己的名字。
話大家都會說,但不同的地方和階級有不同的口音,到今天仍然如此(記得百老匯曾有一部熱門並曾拿下奧斯卡獎的電影《窈窕淑女》,是改編自蕭伯納的戲劇《賣花女》)。尤其是女人,是眾所周知愛說話、八卦、喋喋不休、嚼舌根、嘮叨、碎碎唸、造謠、健談等等,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滔滔不絕。相較之下,一般男人,特別是英國人,刻板印象是沉默寡言、含蓄拘謹。男人善於公開演說及書寫表達,女人則被視為天生的社交高手,因為她們熱中於跟姊妹淘聊天及大談八卦。
英國女人思考並撰寫有關她們自己交友的情形,在十七世紀會更容易觀察到,當時更多女人會寫字,留下大量的文字紀錄,從信札、日記到詩詞及戲劇都有。在過去以男性作者為主的文學世界中,有兩個題材是多數男作家沒有提到的,現在浮上檯面:女人身為媽媽和女人身為朋友的角色。英國女詩人凱瑟琳.菲利浦就在她的詩集中針對這兩個題材,寫到女人之間的友誼無人能比,彷彿在她之前英國沒有作家知道一樣。
凱瑟琳.菲利浦
凱瑟琳.菲利浦(一六三二~六四年)本姓為佛樂,是一名富有的倫敦商人和第二任妻子所生。八歲時,她進入哈克尼的莎曼夫人學校,在那裡她認識了幾個重要的朋友,第一個是瑪麗.奧布瑞,凱瑟琳在詩中稱她為「羅仙娜」。父親過世後,母親改嫁,她就搬到威爾斯。凱瑟琳當時未滿十七,嫁給一個五十四歲的鰥夫,名叫詹姆士.菲利浦。她生下兩個孩子,一個兒子出生兩個禮拜便夭折,一個女兒長大後生了十六個孩子。雖然這段婚姻明顯既穩定又幸福,但對她來說更重要的人似乎是其他年輕女人。
在凱瑟琳成為人妻後,她的筆更是動個不停,目的就是為了讚美羅仙娜:
我靈魂的靈魂!我的喜悅,我的冠冕,我的閨密!
………………
我只想毫不保留地對你揭露,
你也別想對我有所隱瞞。
你的心將我豐富的祕密鎖了起來,
我的胸部是你的私人儲櫃。
凱瑟琳強調兩個女人之間自由分享的私密話。亙古以來,最要好的朋友經常被定義為可以向對方訴說一切,即使是最私人的祕密。

當羅仙娜結婚時,凱瑟琳選擇安.歐文作為她新的最好閨密,並在她的詩中幫她取了「露卡西亞」的暱稱。凱瑟琳則為自己取名「奧林達」,以下我們就稱呼她這個名字。在〈論羅仙娜的變節與露卡西亞的友誼〉中,奧林達對於失去從學生時代到她結婚這段時期的朋友,感到悲嘆不已,讓她想從羅仙娜那裡取回自己的靈魂,讓她可以將它送給露卡西亞:
偉大的友誼靈魂,你跑去哪了?
你現在要何去何從,才能讓我的心頭平靜?
………………
然後只能投向偉大的露卡西亞,
在那裡,重新振作,找回卓越與力量。
………………
露卡西亞和奧林達會給你
永恆,甚至讓友誼長存。
為了露卡西亞,奧林達寫了一封最熱情的詩。她對她大喊:「我們都信仰愛情。」多虧了露卡西亞,她從未曾感到孤單,因為她們兩人的心「可說是合而為一」。在另一首給露卡西亞的詩中,奧林達表達出的感情相當接近同性朋友可容許的情欲之愛:
直至此時此刻,我才知道我從來沒有活過,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希望我這麼說沒有罪過:
我不是你的,而是你。
她覺得可以自由宣布她對另一個女人的愛而不怕遭到報復,因為,如她所說,她和她的朋友是合二為一,也就是一個靈魂。因此,她很確定沒有人會將她柏拉圖式的願景誤當成肉體的渴望。
英國查理一世的皇后亨利埃塔.瑪麗亞推展的新柏拉圖概念,在英國宮廷相當受到歡迎,奧林達因此對女性友誼的本質相當清楚。柏拉圖式的愛的概念來自柏拉圖的《饗宴》,受到十六世紀新柏拉圖人文主義者的信奉,將性愛降級成為純粹的踏腳石,然後拾級登上神聖的愛。根據一般的了解,女人可以和她最要好的閨密共享一個靈魂,然而卻很少會和她的丈夫這麼做。
當露卡西亞也決定要結婚時,奧林達理所當然害怕她會失去第二個靈魂伴侶。雖然她發現露卡西亞選擇的丈夫沒什麼好羨慕的,但奧林達陪著露卡西亞到她在愛爾蘭的新家,結果證明這是一次相當不令人開心的造訪― 丈夫有時擋在兩個好姊妹之間,經常讓妻子抱怨不已。奧林達在露卡西亞婚後直率表達了這個衝突:「我發現在這個世界上友誼很少有不受婚姻影響的……我們通常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朋友的婚禮就是友誼的葬禮。」
根據女人的經驗,婚姻與友誼水火不容,這絕非十七世紀獨有的現象。我們發現在說英語的其他地方也有。舉例來說,十八世紀末的美國,當露西.歐爾寫信給她的朋友波麗,大聲叫嚷說,婚姻是「女性友誼的毒藥」。她希望「如果我們結婚」,那個情況不會發生在她們身上。英國傑出古希臘學者珍.哈里森在她一九二五年的《學生生活回憶錄》中加入個人的哀悼:「婚姻至少對女人來說,妨礙了我生活中兩件光彩的事……友誼和學習。」在今天的流行文化中,小說《BJ單身日記》和電視影集《六人行》就是玩恐婚的哏:怕婚姻會摧毀珍貴的友誼。最近在舊金山,一個三十好幾的單身女人充滿信心地談到她多數已結婚的好姊妹身上的改變時,並說出了這個罪魁禍首:「我的朋友正在快速流失。」
雖然奧林達造訪新婚友人露卡西亞在愛爾蘭的家是一次相當令人沮喪的經驗,卻意外讓她多了一本著作──完成法國劇作家皮耶.高乃依的《龐培之死》的翻譯,這讓她立即一炮而紅。不過,她享受文學盛名的時間相當短暫,不久之後即於一六六四年死於天花,享年僅三十二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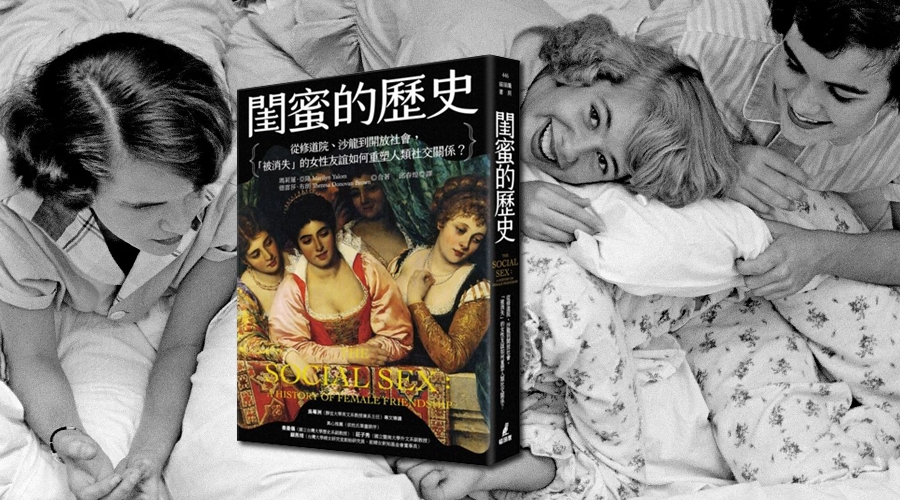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閨蜜的歷史:從修道院、沙龍到開放社會,「被消失」的女性友誼如何重塑人類社交關係?》 The Social Sex: A History of Female Friendship
作者:瑪莉蓮.亞隆(Marilyn Yalom)、德雷莎.布朗(Theresa Donovan Brown)
出版:貓頭鷹
日期:2022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