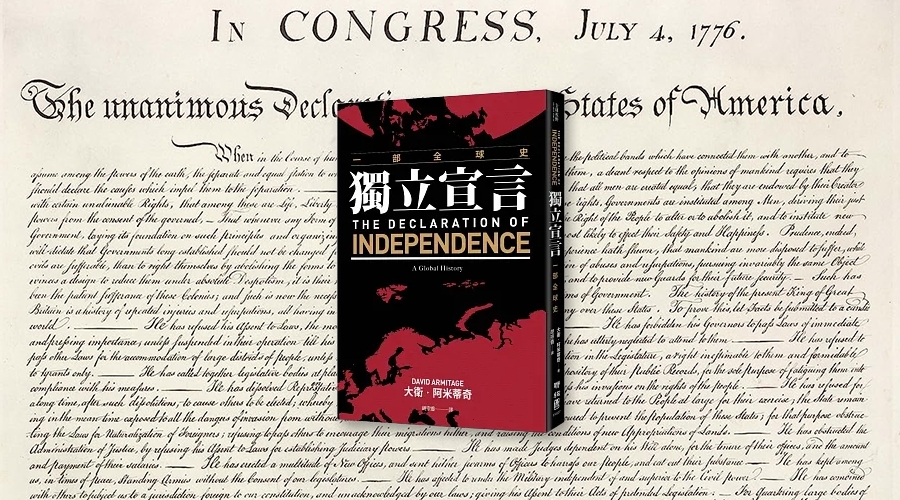
文本以詞說,而始
真理於首行,而明
──Francis Ponge,〈the Fable〉
作為通常是政治文體的「宣言」,特有一種弔詭的書寫姿態。宣言的撰寫或起草人並不代表自己發聲,他們在宣言上署名,卻不是宣言力量的由來;宣言宣告了一個共同體的存在、一種立場的宣示,因而具有力量,然而,在宣言現身之前,它們並不存在,它們簽署了宣言,被宣言所召喚而生,卻不在宣言上署名;起草者撰寫了宣言,通常在其上署名,但卻不是宣言力量的本源,甚至,在大部分時候,他們的存在可以直接忽略,除非像是《獨立宣言》這樣知名的宣言,否則人們很少在意宣言的起草者。
據說是《獨立宣言》主要起草者的傑佛遜,對於宣言弔詭的書寫姿態有複雜的情緒。他一度希望這份宣言可以「更像傑佛遜一點」,傑佛遜起草的初版宣言控訴的奴隸制,指控英王喬治三世對黑人民族的奴役是一場發動反人性的殘忍戰爭。所幸後來的版本拿掉了這些內容,畢竟一群奴隸主署名一份反奴隸宣言太過偽善。
與傑佛遜不同,亞當斯對於《獨立宣言》並沒有特殊情感,他將宣言單純視為一份精要的總結,這份宣言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起草人(們),儘管他對美洲革命的爆發深感驚訝,但正如他在提交最後修改意見後,寫給妻子阿比蓋爾的信中所說,宣言的誕生不過是從1761年美洲大陸與英國本地就〈援助令狀〉(Writs of Assistance)所產生衝突的延續。
兩個《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對於宣言有不同的態度,也同樣都無法決定這個文本應該如何被閱讀。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的《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則以一個不同的角度,一個「文本影響」的角度,來探究這份宣言對於世界,乃至於對全球的衝擊。
在阿米蒂奇看來,《獨立宣言》的「獨立」論述中,有兩個重要的要素:第一,獨立的政治論述是一個向國際社會,向虛擬的世界法庭的陳述;第二,獨立所陳述的政治理念──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並不是人類社會中全新的理念,而是彼時在歐洲大陸已經蔚然成風的國際法理念。正如傑佛遜對於《獨立宣言》原初目的的闡述,他說:
要申明理由,我們就覺得得向世界法庭上訴比較妥當。這也是制定《獨立宣言》的目標。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找到某種過去從未有人想到過的新原則或新論點,也不是言古人未曾言,而是要向世人陳述相關的最基本常識。
回頭看《獨立宣言》的序言:「在有關人類事務的發展過程中,當一個民族必須解除其和另一個民族之間的政治聯繫,並在世界各國之間依照自然法則和自然神明,取得獨立和平等的地位時,出於對人類公意的尊重,必須宣布他們不得不獨立的原因」。這個表述也概括了18世紀國際政治的幾個假設:在國際社會中互動的成員,彼此之間是相互獨立與平等的,新的成員如果出於緣由,而必要做出變動,就有義務向世界公眾,向人類公意,告知其理由。
宣告對象的改變,從對大英帝國喊話,再到對世界公眾喊話,意味著聯合一致的殖民地,已經不再是大英帝國的成員,而是國際社會的一分子;而宣告的內容,也並非任何「革命性」的新事物,而是依據國際法理,對於國家根本條件,也就是「獨立」的確認。當時的國際法經典準則,瓦特爾(Emer de Vattel)所著的《國際法》一書中,如此表述「獨立」對於國家地位的重要性:
任何一個群體,不論採取什麼形式,如果不依賴任一外國勢力,而能夠實現自我管理,就可以稱作一個主權國家。這個主權國家與任何其他國家,享有同等的權利,主權國家是生活在國際法治下自然社會中的道德人。任何人群要加入這一個偉大的社會,必定要先真正擁有主權並實現獨立,也就是擁有權威,與自己的法律,實現對這一既定人群的管轄。
因此,阿米蒂奇強調,《獨立宣言》要向世界傳達的訊息是:「美國革命其實根本不具備革命性,美國人所做的事情,是對歐洲政治理念的強化,而不是背離它」。然而,這並不表示《獨立宣言》完全沒有任何新意,作為政治行動的宣言,不能簡單理解成「防衛性」(defensive)行動,其新意在於,對於一個政治共同體來說,需要透過什麼樣的行動,來宣告自己是國際社會中獨立自主成員,《獨立宣言》具有示範性的典範地位。
在闡述《獨立宣言》的理念性先驅地位後,阿米蒂奇也細緻研究了世界各地「獨立宣言」對於美國《獨立宣言》的致敬。最知名的自然是18世紀另外兩場成功的革命,也就是法國革命與海地革命。1790年,拉斐德侯爵將打開巴士底監獄的鑰匙交給潘恩,請他轉交給華盛頓。對於潘恩來說,這把鑰匙象徵「美國原則輸出歐洲」的成果,是美國革命的原則解放了巴士底監獄,從而解放了法國人民,所以這把鑰匙才能「盡其所用」。美國國父們對於海地革命的看法不一,涉及他們對於美洲革命「基進性」的不同認知,不過這都無礙於「獨立」理念對於基進政治革命的召喚。
這個「宣告獨立」浪潮也包括19世紀初西屬美洲的多場獨立運動,甚至是18世紀中一些失敗以及曖昧的「獨立」案例:從秘魯、波蘭、愛爾蘭、瑞典與比利時,再到日內瓦、巴伐利亞、薩瓦、米蘭與那不勒斯等等,從北歐到南歐,從加勒比到西屬美洲,出現了二十多個借鑒《獨立宣言》的「獨立宣言」。正如阿米蒂奇所說,此後獨立「這個具體而獨特的觀念,在1776年以後的數世紀,逐漸具有某種近乎普世的意義,原因就在於美國的榜樣,在全世界到處傳播」。而其對現實政治格局的影響是,一方面,主權國家取代帝國成為人類政治社會的基本共同體想像;另一方面,吊詭地是,一旦一個國家完成了獨立自主的自我宣告,它也就同時抵制內部對於政治一致性的挑戰,例如美國佛蒙特獨立企圖的抵制,國家的主權與獨立爭議,也就越來越聚焦與侷限在領土問題上。
阿米蒂奇指出,《獨立宣言》的劃時代意義,就在於它為「國家如何獨立」樹立了行動上的典範,而這也成為美國獨立之後的國際法新問題。像瓦特爾那樣的自然法現代闡述者,確實曾經主張國家享有生存,獨立與平等的權利,但那些此前並未享有上述權利的新興國家,究竟要採取什麼手段才能獲得這些權利?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為18世紀末有關國際法討論中的核心論題,部分原因就在於國際社會要回應《獨立宣言》提出的國家主權承認問題。
而宣告獨立也並不僅僅只是單純宣告其作為完整國家的國際身份而已,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在美洲革命一個世紀後指出,《獨立宣言》的出現重新界定了人們對「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理解,儘管在大英議會傳統中,已經存在「人民作為主權者」的理念,但直到18世紀發生在美洲與法國的這兩場革命,人們才真正意識到人民作為主權者的基進意涵。終生信奉大英混合政體理念,因而與其他建國國父格格不入的亞當斯,也不得不接受人民是「一切權威源出與一切權力來源」,人民主權這個「全新、奇異而且糟糕的信條」,這種「用自己雙手創建一整棟大廈」終將深植人心。
書籍資訊
書名:《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作者: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
出版:聯經
日期:2023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