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偉人會降生兩次:第一次是作為凡人,第二次是作為天才。
──維克多·雨果

文|蕭育和
1806年,甫完成《精神現象學》的黑格爾,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及了拿破崙,他將這位在兩年前靠著戰功稱帝的帝王稱為「世界的精神」。當黑格爾看著這樣一個「個體」,騎在馬上專注於一件事情,在這個世界掀起波瀾時,他的心中泛起奇妙的感受。拿破崙對黑格爾來說有種難以言喻的吸引力,他多次提及這種感受,其中包括了後來知名的「歷史終結」段落。
黑格爾不是彼時唯一一個對拿破崙另眼相待,視其代表某種歷史精神的人,為拿破崙所折服的人在後世更大有所在。拿破崙在他與他身後時代所配享的魅力,跟他在世界史中彷彿流星般的存在形成強烈對比:25歲的拿破崙還只是個基層小軍官,十年後他登基成為皇帝;在拿破崙稱帝的十年後,波旁王朝即宣布復辟。拿破崙的人生與他所處的時代都彷彿加速般,在短短的時日裡成就難以想像的偉業與效應,逼得歐洲列強在他敗走後齊心以神聖同盟,來遏阻他所代表的精神,以及他的帝國對歐洲的衝擊。
黑格爾感受之複雜,來自於他眼中的拿破崙是個時代交會的人,並不單指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續對歐洲世界的衝擊,而是拿破崙在他那短暫,卻又波瀾壯闊的一生,所展現出來的精神品格,兼具了古典時代的英雄氣質,而其質地卻又是新生資產階級世界的「凡人」底色。托克維爾曾經指出,在民主天命取代貴族王權支配世界的新時代中,人們對於歷史因果的論述也會隨之改變,貴族時代的歷史敘事主調是「特定個體的意志與情緒」,而在民主時代,則傾向於從「最微不足道的特定事件」中,尋找「宏大的普遍因果」。
拿破崙那時代交會的精神氣質很難如此截然的切割。人們普遍接受,拿破崙的崛起象徵「現代」的降臨,十九世紀美國最受歡迎、最有影響力的作家愛默生,盛讚拿破崙是白手起家的典範。就像後來的資產階級經典形象那樣,拿破崙務實、工作勤奮、性格與舉止有些粗鄙魯莽,而正是這個靈魂中全無高雅,婚姻軼事全無舊時代貴族家庭氣息的拿破崙,成就了一個凡人仰望的非凡。拿破崙的崛起意味著,從此世界歷史舞台的主角即將易主。
而讓黑格爾動容的,是拿破崙的「凡人」底色,他反覆以「個體」來稱呼拿破崙,意味著其存在,同樣也是民主天命下的芸芸眾生,而非任何舊世界王朝血脈的延續。然而,也正是這樣一個凡人,憑藉著驚人的意志,卻改變了人生與他的國家,甚至於整個世界,這又如何的與群氓時代的平庸精神氣質迥異,以致於尼采堅稱「拿破崙像是通往另一條路的最後一個路標」,拿破崙在尼采眼中是一個不甘於眾生碌碌平等的貴族美德形象,是一個「最為孤立而過時」的人。
愛默生筆下的拿破崙是資產階級時代的先行者,而在尼采眼中他是生不逢其時的英雄,兩種形象既互相衝突,又完美的鎔鑄在拿破崙身上。拿破崙的形象也是大革命精神遺產的縮影,本來,大革命就是一個既相信「沒有偉人的偉大時代」即將來臨,又同時堅信只有某種「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英雄氣魄,才足以創造革命新世界的唯意志論事業。正因為拿破崙的精神氣質與形象如此耀眼又難解,在史學家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經典的巨著《拿破崙》一書,幾乎不見拿破崙這個「個體」,一種或許沒有拿破崙的「拿破崙時代」。
與之不同,約翰遜(Paul Johnson)這本短小的《拿破崙》從不於吝評論拿破崙個體這個人,它賦予了拿破崙一個頗耐人尋味的「反英雄」形象。約翰遜一開頭就將拿破崙定調為「機會主義者」,善用後革命的時代機運為自己謀奪了至高的權力。而不若黑格爾、愛默生乃至於尼采,拿破崙所揭露的「現代」,實際上是一個人類即將在兩個世紀後所見證,更為殘酷與晦暗的未來:領袖崇拜、秘密警察,以及極權主義,人們也就不需要意外,二十世紀的獨裁者,從墨索里尼、希特勒、列寧、史達林與毛澤東,再到金日成、卡斯楚、裴隆、海珊、齊奧塞斯庫與格達費,都對拿破崙情有獨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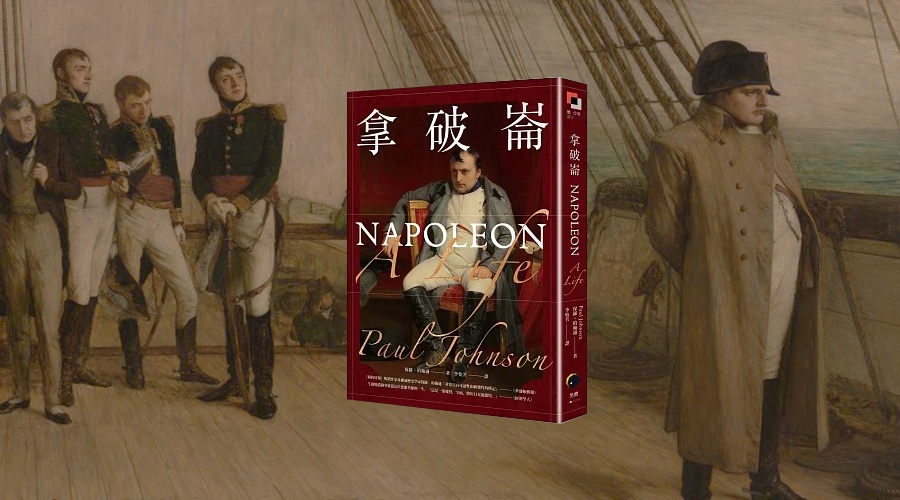
拿破崙所提示的「現代」,遠遠不是歷史的終結、資產階級的勝利或者群氓的時代,而是對暴力的迷信,拿破崙為後世留下的是「對軍事力量的膜拜」,他的信仰「託付在刺刀與槍砲上」,武力是拿破崙唯一懂得的語言,因此,拿破崙敗北後的命運某種程度上也是他的暴力迷信所致,「武力最終也對他做了充滿敵意的宣判」。
軍事才能是拿破崙往後備受推崇的主因,雖然這點很少在黑格爾、愛默生與尼采的評價中體現。奠定拿破崙往後專政地位的義大利戰事,在克勞塞維茲看來,無疑違背了「戰略學中的幾何法則」,但卻是觸及了「戰爭靈魂」的出色行動。拿破崙發動的戰爭,在約翰遜看來是兩次慘烈世界大戰的前奏,克勞塞維茲在《論戰爭》中相當程度上也持此說:
彼時所採取的手段沒有明顯限制,其限制被淹沒在政府及其臣民的能量與熱情中。由於戰爭手段及其後果的多樣,再加上強大的激情,戰爭中的能量被無限提升。戰爭行動的目的是敵人的垮台,而只要敵人還沒有失勢,戰爭就不會停歇。
戰爭性質的改變是現代世界的一大特徵,正如鄂蘭後來所說,戰爭從一種促成和約與聯盟,有限控制傷害的政治手段,徹底質變為甚至不惜同歸於盡的全面性摧毀。威尼斯共和國在拿破崙手上的覆滅,其意義遠遠不是強權凌弱,而是歐洲舊時代的文明秩序,在軍事力量以及強人意志面前,其實脆弱不堪,一個文明的舊時代就此遠去,而由拿破崙所開創的暴力時代正拉開序幕,拿破崙身後被反覆精進運用的戰術,都在往後的世界製造了更大規模的傷亡,也徹底瓦解了歐洲的戰爭規範。而在托克維爾的政治著作中,拿破崙一直都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不只是因為他所建立的中央集權行政體系,在托克維爾看來扼殺了歐洲地方自治的民主傳統,更是因為在後革命時代,軍人奪政將成為共和民主揮之不去的隱憂,托克維爾的這段話,既是對拿破崙一生際遇的總結,也表達了哲人對於「拿破崙」所象徵的隱憂:
隨著革命所激發的熱忱消失…其政府也變得更加軟弱…而此時,軍隊開始了自體組織,開始變得強大,贏得了聲望;偉大的將領也隨之出現。在整個國家喪失目標與熱情時,軍隊則維持了一貫的目標與熱情。公民與士兵…構成了一個兩方拉扯的世界,一端放開繩索,另一端就會收緊。
在約翰遜的《拿破崙》中,一個隱而不顯的對比人物是華盛頓。拿破崙與華盛頓的生涯軌跡有諸多相似,然而其精神氣質卻大相徑庭。對比拿破崙的進取,華盛頓是美國建國元勳中最嚴格自我要求「紳士品格」者,約翰遜對兩人的評價,就像後人對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不同評價一般:美國革命是一場珍視古典政治文明遺產的現代革命,而法國革命是向著敗壞的現代一往無前的野蠻革命。將「軍事的勝利轉化成文明進程」的華盛頓,所嘗試抗衡的是現代對於暴力的崇拜,而將戰爭技術琢磨到連克勞塞維茲都讚嘆的拿破崙,卻帶著時代向更殘酷未來加速前進,一如其結語:
波拿巴主義的巨大罪惡──戰爭與武力的神祇化、全能與集權的國家、以文化造勢活動來神化獨裁者,指揮整個民族去追求個人與意識形態的權力──在二十世紀終於達到了令人可恨的成熟,這將會被歷史紀錄為一個惡名昭彰的時代。
拿破崙及其所謂的暴力信仰是否需要為二十世紀的血腥殺戮負責?約翰遜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即便不是拿破崙本人,至少那些對拿破崙投以英雄崇拜的文人與政治家,也需要負起一些責任。這樣的筆法頗超乎想像,試想即便在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皇皇巨著中,極權主義的因子也追溯不到拿破崙身上,對於拿破崙,約翰遜提出了一個完全有別於黑格爾、愛默生與尼采的視角,然其說詞之成理,又在於緊扣拿破崙於後世最為人所記的軍事才能上。
萊斯(Simon Leys)在其小說《拿破崙之死》中,虛構了一個拿破崙安排了替身,然後逃離聖赫勒拿島的故事。潛回法國的拿破崙不僅沒有如他預想受到熱烈歡迎,沒有人相信他就是拿破崙本人,而替身的過早離世,讓拿破崙發現他所面對的是他不可能擊敗的對手:人們記憶中的拿破崙。
拿破崙是一個凡人,而其短暫的輝煌,又讓他成為「神話」。拿破崙是時代命運之人,他的名字無疑命名了一個時代,而「拿破崙」的意義卻可能注定是一個「謎」,可能提示了歷史的終結、見證了新世界的道德觀、不合時宜的進取德行,抑或是在往後幾個世紀裡延續直到當代,對於暴力的執迷。
對於拿破崙這位命運之人謎一般的「現代性」意義,讀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判斷,這也正是拿破崙的魅力所在:作為一個時代的凡人因而得到青睞,而他非凡的成就,則讓他不可能以一個凡人的方式被記住。
(本文為《拿破崙》推薦序)
書籍資訊
書名:《拿破崙》 Napoleon: A Life
作者: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
出版:黑體文化
日期:2023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