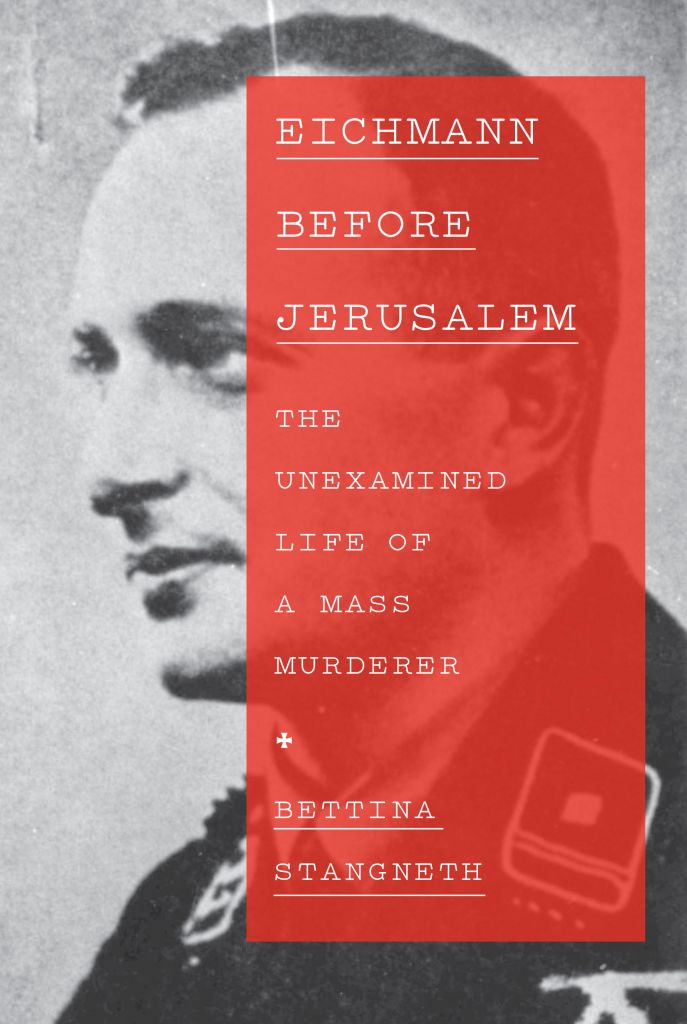
文|Tom Teicholz
譯|蕭育和
像是被保存在琥珀裡的化石,在阿根廷被綁架,在耶路撒冷站著等待審判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作為「玻璃帷幕裡的那個男人」定型在公眾記憶中,雖然肯定是由以色列地方法院三位法官做出判決,並把艾希曼送上死刑台,但伴隨艾希曼走入墳墓的,恐怕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拋送出來,「惡的庸常」(banality of evil)的人身化這個表述。
從鄂蘭的耶路撒冷報導中分離出來的「惡的庸常」這個表述,一直把艾希曼說成是納粹滅絕機器中的小小官僚,推進文書作業,宣稱自己只是遵從上級命令來試圖迴避責任,擺脫個別罪責因他只關注大規模屠殺的效率,或者,如德國哲學家史坦妮思(Bettina Stangneth)所說,「一個被極權體制轉變成全無思想(thoughtless)謀殺者的尋常人」。
自從艾希曼1961年被捕獲後,關於他的書、報導、紀錄與電影累牘面世,但都沒有鄂蘭對艾希曼的刻畫來得深入人心,即便是完全沒有讀過她作品的人。在《耶路撒冷前的艾希曼:大屠殺劊子手不為人知的生活》一書,史坦妮思不失時宜地援引盧梭的話:「每個導致不義的假設,總是牽涉兩方:做出宣稱的人,以及其他深信不疑的人。」史坦妮思──這位漢堡的哲學家──挑戰了鄂蘭的觀點,她論稱我們不應該只就艾希曼自己的話來檢視他,而是要檢視他的話,來理解他的謊言。
在這本頗具說服力的作品中,史坦妮思回顧了艾希曼遠至1937年的寫作、同時代人關於艾希曼的作品以及其他許多訊息來源,有些方甫公開:包含艾希曼曾經嘗試寫的自傳,大量的「阿根廷手稿」;荷蘭納粹共犯薩森(Willem Sassen)與艾希曼在阿根廷厚達1600頁,60幾卷帶子的訪談,有些有薩森的註解,有些則是艾希曼親手註解;艾希曼在布宜諾賽利斯被捕的審問謄本;耶路撒冷審判期間的審問與書寫,包含他另寫自傳的意圖,以及最後寫給家人的書信。
史坦妮思的作品遠遠不是艾希曼罪惡一生的年代排序而已,它講述了艾希曼怎樣依據不同的聽眾量身打造他的說詞,以及其他人怎麼看待他,艾希曼是個用各種謊言打造自己形象,耽於浮誇與精心算計的脫罪的男人。
身為蓋世太保一員,早在維也納的納粹國安部門任職,並負責奧地利的猶太移民開始,艾希曼就已經迫切渴望得到賞識。靠著自修成為猶太人事務專家,艾希曼成功讓人相信他出生於德國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地薩羅納、相信他能讀能說希伯來語與意第緒語(他是能強記一些慣用語)、相信他對猶太律法與教儀涉獵甚深、同時跟猶太領導人混得很熟(他是能丟出一些人名做做效果)。
艾希曼很早就用猶太人事務來親近納粹層峰,他負責督導布拉格與羅馬尼亞的強迫遷移猶太人事務,以及從斯賽新、波森與柏林等地驅逐猶太,靠著被拔擢為處理猶太社群的專家,艾希曼成功打入納粹高層,以鬼才問題解決家而為人所知(假如「問題」意指「猶太人」)。正因如此,當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在萬湖會議被賦予策畫猶太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時,艾希曼很自然地當仁不讓。他還特別到庫爾姆集中營去看活動毒氣車,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去看屠殺猶太人。很多年後在阿根廷,艾希曼還向薩森宣稱,「最終解決」是他創造的詞彙,可是到了耶路撒冷的審判,艾希曼又改口在那場會議,他只是負責紀錄的秘書。
在布達佩斯,艾希曼的生涯另起新頁,1944年,在約莫四個月的時間裡,艾希曼籌畫了押送42萬猶太男女老幼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死亡急行任務,很多年後在阿根廷,艾希曼依然洋洋得意,「這可是前無古人的成就!」到了耶路撒冷的審判,艾希曼又宣稱他跟布達佩斯猶太領袖的協議,足以證明他當時致力於營救匈牙利猶太人,可是,在阿根廷,艾希曼又侃侃而談他如何愚弄這些猶太領袖。
在紐倫堡大審上,艾希曼的納粹同夥,像是Dieter Wisliceny與Kurt Becher,為了脫罪,指控艾希曼「失去控制」、習慣性地誇大自己跟希姆萊的私交、近乎病態地熱衷於遣送更多的猶太人(即便希姆萊已經下令停止)以及酗酒等等。Wisliceny接著在紐倫堡作證,艾希曼一直以來都問心無愧,並告訴他「無論到哪裡他都會追隨元首,至死不渝…」
艾希曼甚至還是六十萬納粹屠猶這個統計數字的由來,納粹份子Wilhelm Höttl在紐倫堡大審中作證,艾希曼統計有四十萬猶太人死於集中營,另有二十萬則死於黨衛軍特別行動隊之手,這個說法也在出現在布達佩斯猶太領導人Kasztner的口供中,媒體接著捕捉到了這個數字並添上一句:「六十萬猶太人的大屠殺。」
二次戰後艾希曼的人生又有了新的轉折,史坦妮思舉細靡遺地記錄了各種細節。艾希曼很早就開始準備假身分計畫逃亡,所以,假如他的確曾向Wisliceny說會追隨元首「至死不渝」,顯然是在說謊。他以Otto Eckmann的身分在美國的戰俘營度過他戰後的頭幾個月,此後,他順利逃脫並換上Otto Heninger新身分,在德國北部落腳,他在那裡低調地過了五年。艾希曼甚至聲東擊西,讓很多人相信他已經逃往中東,在大穆夫提(Grand Mufti)的庇護下定居在開羅或大馬士革。
1947年,艾希曼的妻子薇拉,申請宣告她的丈夫死亡。彼時納粹獵人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收到消息提出抗議,說這不過是艾希曼詭計的進化,好引起全世界追緝他的興趣。1950年,艾希曼尾隨了一條納粹戰犯預先安置的逃脫路線,逃到了熱那亞,在那裡他以Ricardo Klement的身分拿到了簽證並登上往布宜諾賽利斯的船。艾希曼的短期簽證來自於Horst Carlos Fuldner,一個得到阿根廷領導人裴隆(Juan Perón)批准的人蛇集團首腦。1948年,同樣在這個南堤洛邦區城市,艾希曼、「奧斯威辛的死亡天使」Josef Mengele,以及希姆萊的助手Ludolf von Alvensleben,都被核發了身分證明文件。1962年,艾希曼對於「組織」為他與家人在阿根廷提供安全的庇護表達了感激之意。
抵達阿根廷多年以後,艾希曼解釋了阿根廷的吸引力:「我很了解在這個南美的『應許之地』,我有很多至交好友,在他們面前我可以公開地、自在地也驕傲地說我就是阿道夫艾希曼,前黨衛軍親衛隊中校。」多年後他憶及初抵阿根廷的感覺,「我的心充滿愉悅,怕有人會揭發我的恐懼消失了,我來到這裡,而且非常安全。」
阿根廷與布宜諾賽利斯對這些前納粹份子可謂相當殷勤,艾希曼一再與過去的納粹同事團聚。到了1952年,艾希曼的妻子薇拉為自己與三個孩子申請了護照與旅遊簽證,僅就這個理由,德國官方就應該要知道艾希曼正身處阿根廷(至少是可能)。史坦妮思說明了德國官方甚至以色列探子可能會知道艾希曼身處何地的各種方式,以及他們不讓艾希曼被發現的可能盤算(像是對德國來說可能的難堪,或是想起納粹過去不堪歷史的等等)。無論如何,艾希曼在中東縝密佈建的假行蹤,以及死亡與自殺的謠言,都讓官方裹足不前。
史坦妮思推翻在艾希曼相關電影中根深蒂固的看法,艾希曼在阿根廷惶惶不可終日,生活深居簡出的描述。艾希曼不只跟妻小重逢團聚,他們甚至還在阿根廷又生了一個小孩,艾希曼把這當成是他對抗敵人的勝利。他一點也不避諱身分,一再說「跟總統裴隆很熟,他會為了我們德國人抽空」,自始自終,艾希曼在阿根廷都供職於德國企業,在他被捕時,他正為賓士企業工作,為家人在布宜諾賽利斯郊區買了地,家才剛剛蓋好。
在阿根廷的日子,艾希曼絲毫無懼高談闊論,如史坦妮思特別指出:「艾希曼硬是要講的強烈衝動始終大過他的思危意識。」他向他在圖庫曼的同事暢談,在納粹同情者的聚會上高論,在與薩森的錄音訪談中也講,成篇累牘的手稿上他更要暢談一番。在艾希曼阿根廷期間的寫作跟錄音帶裡的滔滔不絕中,他遠比在耶路撒冷受審時的嘀咕碎念,更有激情與自信說著話,艾希曼深信血統與種族的納粹意識形態,把自己看作某種新人,絕不感情用事、不被宗教與世俗道德所束縛(他說,自覺有罪是幼稚的)、對於個人財富的派頭不感興趣(雖然在納粹任職期間他頗為享受)。德意志種族,或他稱之為「我的血統」,是他奉行的目標。
艾希曼宣稱,是猶太領導人Chaim Weizmann的「干預」,迫使德軍進軍波蘭,而這使得最終解決成為必然。納粹打的是對抗敵人(像是猶太人)的總體戰,要用各種必要手段求得勝利──猶太人什麼都可以做,納粹也同樣什麼都能幹。艾希曼說,這是沒有「雙重標準」的血統之戰。艾希曼與他的納粹同僚並沒有做錯,也就無法入罪,因為雙方幹的都是殘忍的暴行。艾希曼的「惻隱之心」完全不會被他的所作所為所困擾,因為他效忠於他的血統與他的帝國。
遲至1956年,艾希曼才考慮向德國自首說出納粹時期的真相,藉由向當時西德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的公開信,他認定自己會像是其他知名納粹黨人一樣,只有四到六年的徒刑。艾希曼大量閱讀關於大屠殺的書籍,也一直關注Kasztner案,他讀Joel Brand的書,也讀Kasztner案的報告。史坦妮思論稱,艾希曼的目的不是為了瞭解,而是為了發現,當他建構自己的敘事(之後,是他的辯護)時所能運用的弱點。
艾希曼一直持續書寫,早在納粹任職期間,就已經宣稱要寫一本執行最終解決的書,他自稱這個計畫在戰爭結束前被破壞了。戰爭結束後他說要馬上開始寫回憶錄,接著誆稱在離開德國北部時已經焚毀。在阿根廷,他寫了260頁的手稿向家人解釋,以及107頁題為「其他人說完,現在換我要說」(The Others Spoke, Now I Want to Speak)的自傳草稿。
艾希曼在阿根廷對於大屠殺與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完全心安理得,他在一場會議上說:
結論是…我必須先要告訴你們:我完全不後悔!…要發自內心地說我們做錯了什麼我會很猶疑。不,我必須誠懇地告訴你們…假如我殺了一億三十萬的猶太人(歐洲的猶太人口總和初估),我會相當滿意並且說幹得好,我們徹底摧毀敵人了…我們得要完成我們的職責。
面對大屠殺真相,阿根廷的德國人終究放棄了任何復興納粹的希望。裴隆派在1955年失勢,艾德諾在德國也得到了穩定多數。1950年代後半葉,追索納粹戰犯更為積極,德國發布了逮捕令。即使如此,艾希曼在阿根廷也很少掩飾自己的身分。艾希曼不願隱藏身分的高調終於惹來拘捕,從他在1960年五月11號在自家門前的大街上被逮捕開始,艾希曼開始起草自己的抗辯。這是他生涯的第四個篇章,他炮製了鄂蘭很肯定隨意打發掉的第四個人格。
這段時間,深諳審問技巧的艾希曼發現自己身處於耶路撒冷的玻璃帷幕裡,他已經經年準備了回應與獨白,他讀了夠多的現存文獻,深知什麼事實最能操作,在哪裡最能著手懷疑。在以色列,艾希曼把過去拋諸腦後,保證他的阿根廷手稿不會糾纏他,也確認那些可能挑戰他版本的人,要麼大部分已經亡故,要麼從未想過走進以色列法庭。
艾希曼在以色列持續寫作,為他自己構築新的敘事,宣稱他的一生都為哲學家康德的定言令式原則所引導──即便納粹主義已經令他在道德上反感,他也依然奉行更高的律法,也就是對帝國的效忠。艾希曼辯稱沒有人能用不同於他在戰時所採行的道德體系,來審判他的罪,鄂蘭則對此則無動於衷。
當史坦妮思這本書2011年在德國首次出版時,德國媒體的注意力都針對斯坦妮斯宣稱,德國早在1952年就知道,或者應該知道艾希曼的下落。艾希曼直到1960年才被以色列著手逮捕,完全是因為,一如〈明鏡〉週刊所說,「德國還沒準備好,也不願意送他受審。」
在美國,自從這本書在2014年出版以來,許許多多的討論都不是放在艾希曼身上,而是放在鄂蘭,「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是「對」?是「錯」?以至於,紐約時報的部落格刊登了耶魯大學的本哈比(Seyla Benhabib)的貼文,追問「誰在受審?艾希曼還是鄂蘭?」
鄂蘭對艾希曼審判的紀錄在〈紐約客〉刊出後立刻激怒了許多人,因為她不但沒有翔實報導審判,還嚴苛地批評了猶太領袖在猶太區和集中營裡的行為。多年以來,她的評論者認為,最好的狀況就是她其實受到了誤導,因此以為這與艾希曼的罪行無關,但最糟的可能則是她的觀點源自於身為猶太人的自我厭惡,再加上她與納粹同情者海德格有過一段戀情,又得知大屠殺時留在歐洲的猶太人為了求生能做出多麼可佈的事,因此更加強化了這種觀點。
至於艾希曼本人,鄂蘭斷言,他各方面都不特殊:沒有特別聰明或特有教養;在納粹任職之前沒什麼實質成就;身材瘦弱帶著細瑣的聲量反覆循環跳針。鄂蘭寫道,艾希曼對於哲學與服從論題的理解相當貧乏。鄂蘭斷言艾希曼反猶太主義的「庸常」,他效忠希特勒與納粹體制的「全無思想」才讓他犯下種族滅絕大惡。
在史坦妮思看來,鄂蘭沒有理解的是,艾希曼想讓他的「受眾」相信,無論是否可憐,他都是出於不合時宜的忠心而服從命令,是個有良知的人。史坦妮思指出,每一個艾希曼的捕獲者與審問者,都在之後的報告說,他們相信他們對艾希曼來說都是重要的人物,艾希曼一直奉承他們,好讓他們相信。史坦妮思寫道,「一次又一次,艾希曼與他的文本把人們誤導向錯誤的結論。」
當鄂蘭無法像史坦妮思一樣,接觸艾希曼在阿根廷的所有手稿、訪談還有獄中寫作時,她就無法了解艾希曼在戰時怎麼嘲弄良知不過是個謊言、嘲弄所有的悔恨表述都是「廉價的俗套」,或者,偏執的空想家艾希曼怎麼讓他的信條在總體戰超越哲學。
鄂蘭的辯護者解釋,鄂蘭對於「全無思想」的使用,不是要減低艾希曼的罪責,事實上,鄂蘭已經認知到艾希曼對於屠殺負有個人責任。他們論稱,鄂蘭想要解釋的是艾希曼對自己的作為缺乏良知──讓艾希曼犯下大規模屠殺的是他良知的闕如,是艾希曼沒有思考的能力。
鄂蘭在此並沒有錯,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與他書寫中所表演出來的人格,是刻意的掩飾。史坦妮思所要論證的是,至關重要的不是鄂蘭或其他人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想成什麼,而是艾希曼自己把自己想成什麼。艾希曼的真相必須在他的文字整體中,在他遞交出來的各種真相中,以及,最能流露出真相的,在他的謊言當中,才能找到。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期間留下了八千多頁手稿,走上死刑台前他給妻子的遺言是:「我的內心非常平靜,這是我的信念確切無誤的明證。」艾希曼給德國人的最後遺言是:
各位先生,片刻後我們將再度相見。這是所有人的命運,我一生信神,至死不渝。德意志萬歲!阿根廷萬歲!奧地利萬歲!這些是我最為掛念,最不敢或忘的國家。我必須服膺戰爭的法則,必須服膺我的旗幟。而我已經準備好了。
艾希曼看來想讓我們相信他不過就是個愛國者,一個戰時忠貞奉侍國家與奮鬥目標的公務員。艾希曼也許從不是例外,但他狂熱的反猶太主義是有罪的,他熱衷地參與屠殺這麼多無辜猶太男女童稚,更讓他置身人之常理之外。感謝史坦妮思,我們現在更全面地了解他的罪大惡極,就像史坦妮思所說:「一個戴上這麼多面具的人,總是讓人想要揭穿他的一切。」
書籍資訊
書名:《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Eichmann vor Jerusalem: Das unbehelligte Leben eines Massenmörders
作者:Bettina Stangneth |譯者:Ruth Martin
出版:Knopf
日期:2014
原文出處:LARB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