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魯大學政治及人類學學者詹姆斯‧史考特(James C. Scott)在著作《反榖:古代城邦的深刻歷史》(Against the Grain: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中提出質疑主流觀點的相反見解:人類並沒有因為從狩獵採集和遊牧邁入農耕,從此擺脫嚴峻的生存難題。
史考特借鑒過去和最近二十年的考古研究,表明六千多年前出現的農耕從某些方面來看並非進步的過程。例如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終年忙碌於耕作的農村或早期農業社會,這種轉變讓他們犧牲了原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長時間勞動、家畜傳染病、營養不均、收稅徵兵等代價。
史考特認為,無論是農業或大規模定居本身都不會促成國家形成。中東農民在終年耕作的農村出現以前,就已經開始栽種農作物;從游牧轉變為大規模永久定居的原因,主要取決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提供豐富的野生植物和水中生物等食物來源,而不是因為人類開始從事農業。
他表示早期國家的形成是由一群極具野心的統治者,將農業與定居社群強迫結合的結果。國家的形成始於濕地區域,例如肥沃月彎這種蘊含面積廣大的肥沃土壤,糧食產量不但足夠供應給居民,單一作物也能以較小的空間儲藏,更重要的是方便國家控管和徵稅。
但這些剛萌芽的農業國家型態也極為脆弱,經常分裂成更小的政治實體或完全崩潰。史考特認為,研究人員往往忽略考古記錄中的「瓦解」,其中包括居民對戰爭、稅收、傳染病和作物歉收忍無可忍的可能性。

那為什麼人類祖先要放棄原本多元的食物來源,轉移成集中生產風險高的單一作物呢?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真正答案,但史考特推測氣候變化帶來的壓力是可能因素之一。然而,我們至少知道兩件事實:首先,數千年來的農業變革對大多數生活在這種社會的居民來說,實際上是一場災難。考古記錄表明,農民的生活比狩獵採集時過得更辛苦。骨骼化石證據顯示他們的身材較矮小、牙齒狀況更糟、營養不良更嚴重、死亡率也更高。
此外,與馴養的家畜共同生活造成跨物種之間的傳染病,幾乎將密集的社區破壞殆盡。史考特表示,古代農業社會與其說是城鎮,不如說是「新石器時代的多物種集中營」。史考特並不是第一個提出質疑的人,美國演化生物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曾將農業的發明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錯誤」。
另一個事實也能從證據得出,那就是種植穀物與第一批國家的誕生有著至關重要的直接關聯。穀物並不是人類唯一的主食,但它們卻是唯一有利於國家形成的作物。史考特寫道:「歷史上沒有木薯國家,也沒有以西谷米、山藥、芋頭、香蕉、麵包果或番薯立國的國家。」

穀物有何特別之處嗎?確實有,穀物與其他作物不同:它特別易於徵稅。某些作物(如馬鈴薯、番薯、木薯)可埋藏在地底躲過收稅官,就算不小心被發現還要費力挖出來。其他作物(特別是豆類)則有不同的生長週期,或者所有季節都能生長不用隨季節收成。換句話說,收稅官沒辦法在固定時間前來一次收齊所有稅。而用史考特的話來說,只有穀物是「可見、可分割、可估算、易於儲存、運輸和定量」的作物。雖然其他作物也具備某些優點,但只有穀物符合所有條件,因此穀物成為了人類發展的「澱粉類主食、稅收單位和曆法基礎」。收稅官只要評估田地大小和設定稅收額,往後只需定時回來收取該徵收的份額。
書的末尾以亞洲遊牧民族如何劫掠和襲擊早期農業社會作結。遊牧民族透過搶奪鄰居的食物和商品,逼迫對方協商交易換取和平。他們最終成為農業社會的貿易夥伴,為定居型態的社會帶來銅器、馬匹和奴隸等等。偶爾也作為雇傭兵,專門追捕逃跑的奴隸和鎮壓反抗。史考特寫道:「諷刺地是,正是這些『野蠻人』幫助各國成為今日主要的政治主導者。」
史考特沒有將狩獵和遊牧生活方式描繪成烏托邦的制度,而是仔細觀察兩者的優缺點,提供讀者更全面的觀點:進入農耕並不是人類選擇了一種比較合理或簡單的方式生存,更應該說選擇了另一種同樣困難的方式生存,文化也從此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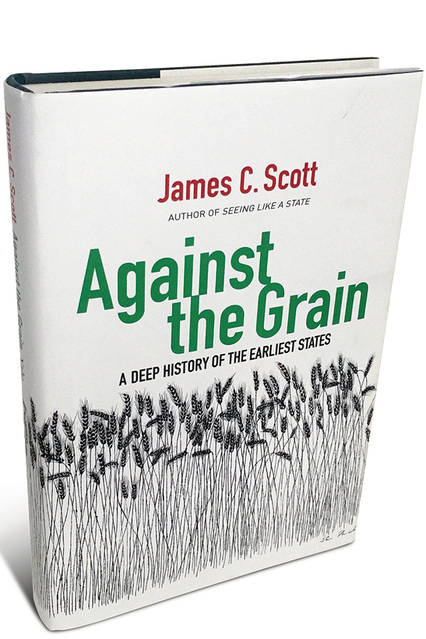
書籍資訊
書名:《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作者:James C. Scott
出版:Yale University Press
日期:2017
[博客來外文館]
2019追加更新:中文翻譯版已出
圖片出處:New Yorker、Pinterest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