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始於約十年前雪城大學黑板上一組潦草的方程式,認知神經學家馬克‧霍華德(Marc Howard,現任職於波士頓大學)和當時的博士後學生卡蒂克‧尚卡爾(Karthik Shankar)想找出時間進展的數學模型:表示過去時間、與神經相關的可計算函數,就像大腦用於描繪記憶與感知的一張心理畫布,霍華德說:「思考視網膜如何作為顯示螢幕提供各種視覺資訊,而時間則用於顯示記憶。我們希望用理論解釋它的運作模式。」
將視覺資訊(如發光強度或亮度)表現為特定變數(如波長)的函數還算簡單,因為眼睛的特定受器直接衡量了所見物質的性質,但大腦並沒有時間的受器,日本大阪大學認知神經學家林正道說:「對於顏色或形狀的感知很直接,但時間有著難以捉摸的性質。」如果大腦要對時間進行編碼,就必須做一些沒那麼直接的事情。霍華德和尚卡爾的目標是在神經層面精確地找出這個現象,他們對此感興趣是因為相信大腦應該存在一些「簡約而美麗的規則」。
他們用方程式描述大腦在理論上如何間接地對時間進行編碼。他們推測,當感官神經元對一個正在展開的事件做出反應時,大腦會把活動的時間部分映射到經歷的某個中介碼(intermediate representation)——以數學術語來說,這是一種拉普拉斯變換。中介碼使大腦能把事件資訊編碼保存為變數函數,而不是保存為時間函數。然後,大腦將中介碼映射回其他活動中,以獲得暫時的經歷——即拉普拉斯逆變換——來重構壓縮後的記錄,以此得知是什麼時候發生。
就在霍華德和尚卡爾準備完善理論的幾個月後,其他科學家獨立發現了稱為「時間細胞」的神經元,它們「盡可能地貼近我們對於過去的確切記憶」。這些細胞在一段時間內被調節到特定的時間段,比如,一些細胞在刺激後一秒放電,另一些在五秒後放電,其實是在經歷與經歷的時間間隔之間架起一道橋樑。科學家能夠觀察細胞活動,並根據哪些細胞放電來確定刺激何時會出現。這是科學家框架中的拉普拉斯逆變換部分,近似於過去時間的函數,霍華德說:「我心想天啊,這些寫在黑板上的東西很可能是真的,就在那時我知道大腦參與了協作。」
由於理論得到了實證支持,霍華德與同事開始研究更廣泛的框架,希望利用這個框架來統一大腦中截然不同的記憶類型。如果他們的方程式是由神經元實現,那不僅可用來描述時間的編碼,還能描述許多其他的特性——甚至是意識本身。
但一切都只是假設,自2008年發現時間細胞以來,科學家只看到一半的證據,而另一半——時間的中介碼——則完全停留在理論階段。
直到2018年的夏天。

2007年(霍華德和尚卡爾開始討論框架的前幾年),阿爾伯特‧曹(Albert Tsao)在挪威科技大學卡夫利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實習,在日後的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梅-布里特‧莫澤(May-Britt Moser)和愛德華‧莫澤(Edvard Moser)的實驗室裡度過了一個暑假。莫澤夫婦發現了網格細胞——負責空間導航的神經元——位於一個名為內嗅皮層內側的大腦區域,而曹好奇其姐妹結構「內嗅皮層外側」有什麼功能。兩個區域都向海馬迴提供主要的輸入,海馬迴生成我們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所發生經歷的「情景」記憶。曹推測,假如內嗅皮層內側負責了地點的反應,那內嗅皮層外側很可能承載了時間資訊。
對我們來說,時間是事件的序列,是衡量內容逐漸變化的尺度。這解釋了為何我們對最近發生的事情比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記得更清楚,也解釋了為何當某種記憶出現在腦海時,我們往往會聯想到同一時期所發生的事情。但大腦是如何構成一個有序的時間歷史?又是怎樣的神經機制使之成為可能?
起初,曹的研究一無所獲,甚至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因為嚴格來說,每件事都有一定的時間屬性。他檢測了老鼠覓食時內嗅皮層外側的神經活動,但他不明白這些數據代表什麼,因為似乎沒有出現明顯的時間資訊。
曹擱置了研究回到校園,沒有再去處理這些意義不明的數據,直到多年後才決定重啟研究,並嘗試對群體的皮層神經元進行統計分析。就在那時,他觀察到一種長得很像時間的放電模式。
隨後,他與莫澤夫婦開始設計實驗進一步測試這種關聯。在一系列實驗中,一隻老鼠被放在一個盒子裡,它在盒子裡能自由地漫步和覓食,而科學家記錄了內嗅皮層外側與附近大腦區域的神經活動。幾分鐘後,他們把老鼠從盒子裡拿出來,讓它休息一下再把它放回去。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內,他們重複做了12次實驗,並在實驗與實驗之間改變牆壁顏色(可能是黑色或白色)。
看似與時間相關的神經行為主要發生在內嗅皮層外側,當老鼠進入盒子時,這些神經元的放電率突然飆升。隨著時間流逝,神經元的活動以不同速率減少。在下一次實驗開始時,老鼠再度進到盒子,而神經元的活動也再次上升。同時,在某些細胞中,不僅是每次實驗而是整個實驗過程中,神經元的活動都有所減少:但在其他細胞中,在整個實驗過程中都不斷增加。
根據這些模式的組合,科學家——或許還有老鼠——可以區分出不同的實驗,並將它們按順序排列。數百個神經元似乎正共同進行協作,記錄了實驗順序與每個實驗的長度。

未參與研究的阿伯尼醫學院神經學家馬修‧夏皮羅(Matthew Shapiro)說:「你得到的活動模式不是單純銜接資訊的延遲,而是在解析經歷的情景架構。」
老鼠似乎利用了「事件」——環境的變化——來瞭解時間過去多久。科學家懷疑,當這些經歷沒有被清晰地劃分為不同片段時,信號可能會因此看起來很不同。因此,他們在一系列實驗中讓老鼠繞著一個8字形軌道奔跑,有時朝著一個方向,有時朝著另一個方向。在重複的任務中,內嗅皮層外側的時間信號重疊了,很可能使老鼠無法區分不同的實驗:因為它們對時間的感知融合在一起了。
曹和同事認為,他們已經開始梳理出大腦中主觀時間背後的機制,一種讓時間被明確標記的機制,夏皮羅說:「這表明我們對時間的感知是很彈性的,一秒鐘能持續到永遠,而一天也能轉瞬即逝。它非常簡潔地解釋了我們看待時間的方式,我們處理按順序發生的事情,而這些按順序發生的事情又決定了我們對時間流逝的主觀估算。」
科學家想知道一切是怎麼發生的,而霍華德的數學模型或許幫得上忙。當他聽說曹的研究結果時,他欣喜若狂:曹在神經活動中觀察到的衰變速率不同,就是他的理論預測大腦中經歷的中介碼應該發生的情況,霍華德說:「這看起來很像是拉普拉斯逆變換。」這正是他與尚卡爾的數學模型所缺少的一部分實證研究。
霍華德說:「就在科學家發現時間細胞的同時,我們把這些拉普拉斯變換和逆變換的方程式寫在了黑板上。因此我們花了10年時間來觀察逆變換,但我們沒有看到真正的變換。現在我們找到了,我很興奮。」
霍華德補充說:「我和同事、學生所做的所有研究都是假設性的,但可能性並非是零。它是一組不存在於大腦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方程式,而我們在別人的實驗室數據中看見了它。」
如果霍華德的數學模型正確,那麼它將告訴我們大腦是如何創建與維繫一個過去的時間軸——他將其描述為「彗星的尾巴」,隨著我們的生活過日子,它會在我們的背後不斷延伸,隨著它越退越遠,我們的記憶也變得越來越模糊與壓縮。這個時間線不僅對海馬迴的情景記憶有用,而且對前額皮質中的工作記憶和紋狀體中的條件反射也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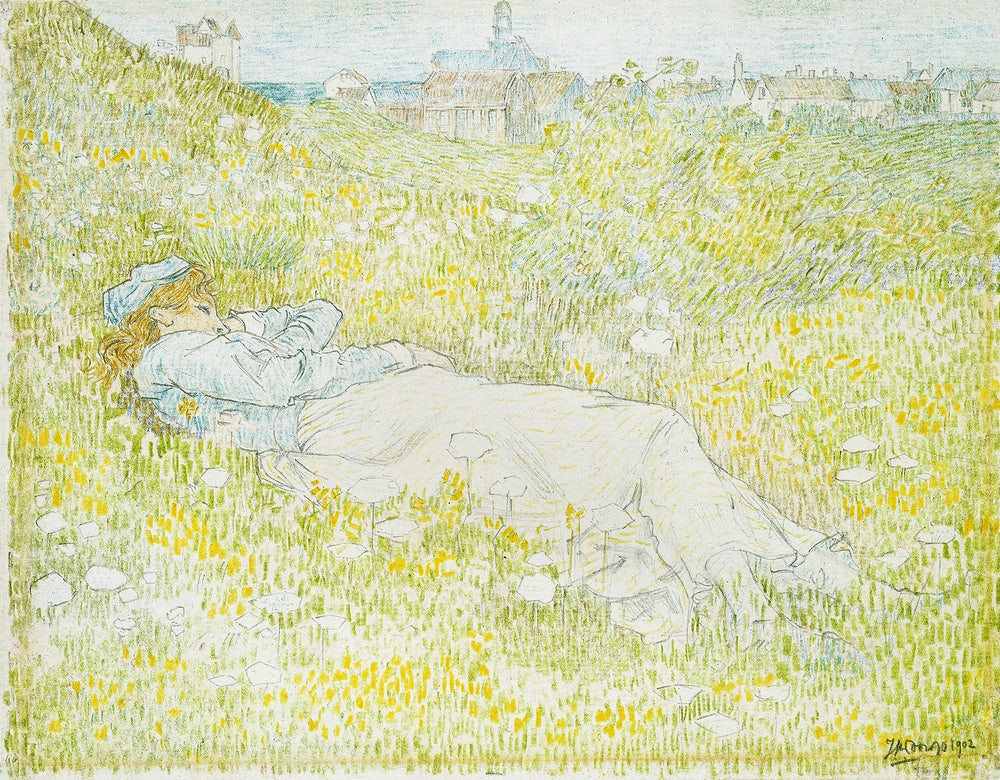
在這些大腦區域中發現的時間細胞似乎支持了這個理論,華盛頓大學的發現表明,猴子在觀看一系列圖像時,其內嗅皮層的時間活動與曹在老鼠身上觀察到的相同,霍華德說:「這正是你所期望的:圖像出現的時間。」
他懷疑,記錄不僅僅是為了記憶,也是作為一種整體認知。他提出,同樣的數學也能幫助我們理解我們對未來的感覺,有助於我們理解時間的意義,因為它涉及了對未來事件的預測(某件事的本身是基於從過去經驗中獲取的知識)。
霍華德的理論也開始表明,大腦用於表示時間的方程式同樣也能應用在空間、數量(我們對數字的感覺)與基於已知經驗所做的決定——實際上,它能應用在這些方程式語言中的任何變量,他說:「如果你能寫出大腦的狀態……數以千萬計的神經元在做什麼……那方程式與方程式之間的變換就是思考。」
但在進行任何應用以前(例如人工智慧),科學家必須確定大腦本身是如何做到的,曹坦承還有很多問題需要釐清,包括是什麼驅使內嗅皮層外側去執行它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是什麼東西讓記憶被明確標記。霍華德的理論提供了有效的預測,使科學家擁有新的方式來尋找答案。
當然,霍華德的數學模型並不是唯一的觀點,例如一些科學家假定由突觸連接的神經元鏈是按著順序放電,這也有可能是另一種變換,而非拉普拉斯變換。但這些其他可能性並沒有澆滅霍華德的熱情,他說:「有可能這些假設都還是錯的,但我們很興奮,也正在努力研究。」
原文出處:Quanta
圖片credit:Jan Toorop,1858–1928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主題總覽
主題總覽 成為粉絲
成為粉絲 追蹤IG
追蹤IG 追蹤推特
追蹤推特 也有串串
也有串串 合作提案
合作提案